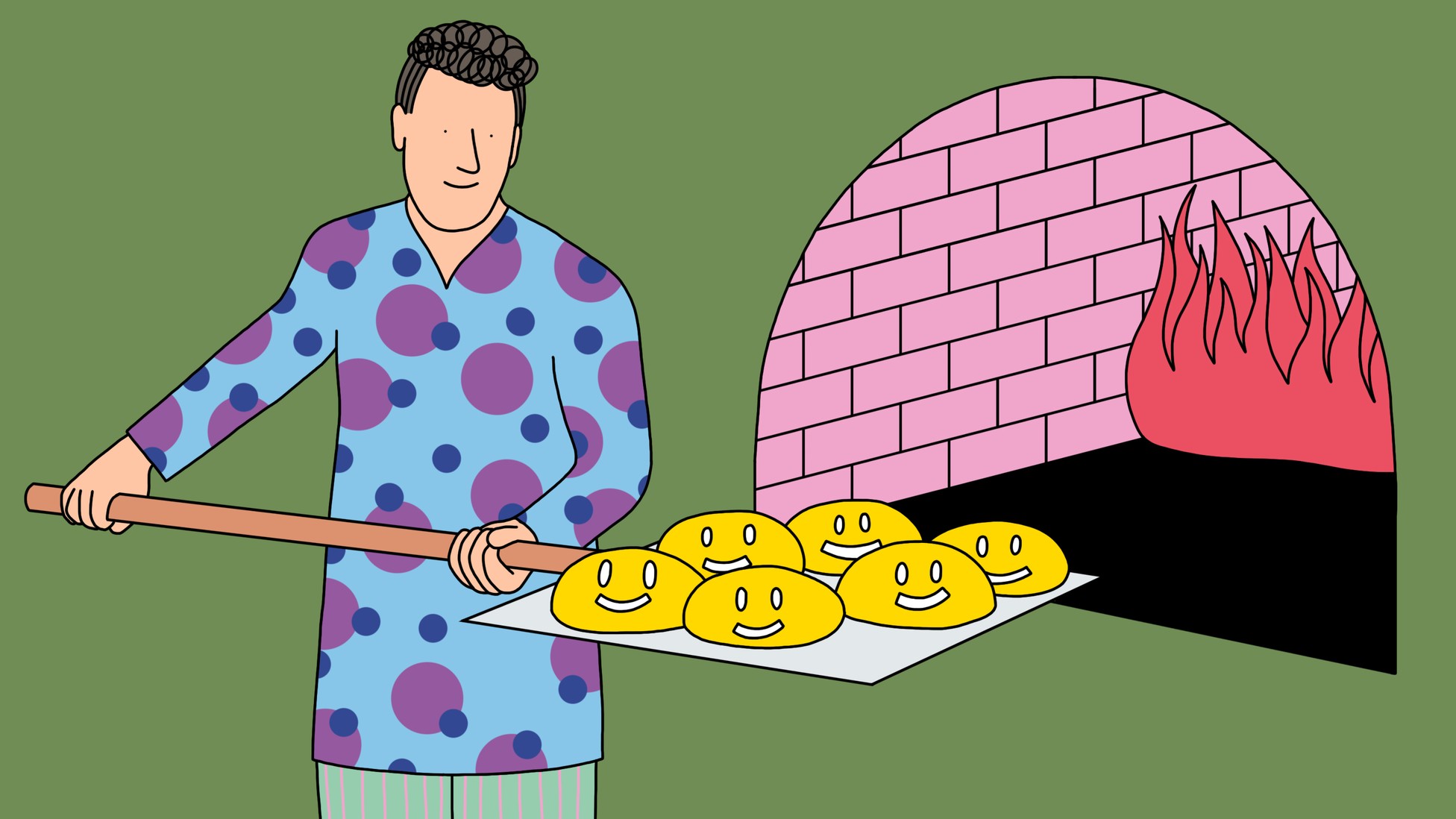编译自《连线》文化版文章,原文标题“Behind the Scenes at Rotten Tomatoes”
作者:Simon Van Zuylen-Wood
翻译:Dkphhh
“由人类,而非算法,为每一部电影打分”
Tim Ryan 是一位电影发烧友,42 岁,顶着一头杂乱的红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罗德岛当记者,没事做的时候就看经典老片,“什么戈达尔啊,还有俄罗斯的红色电影,”他说。后来他搬到了湾区,当时羽翼未丰的烂番茄就在那里。为了看电影,Ryan 成天泡在烂番茄上。2004 年,烂番茄公开招聘,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Ryan 抓住了。现在 Ryan 把自己比作电影《摇滚巨星》里的 Mark Wahlberg 饰演的角色——“从头号粉丝变成了主唱”。
Ryan 是这家影评网站任职时间最长的员工,最近他投身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新项目里。当我 10 月份造访烂番茄的新办公室——现在位于比佛利山——他这么解释这个新项目:“如果烂番茄一直存在会怎样?”
Ryan 想给从古至今所有的电影都打个分,或者更准确一点,把从古至今每一部电影的每一篇影评都搬上到烂番茄上。
世界上的第一部剧情长片(feature film)是《凯利帮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Kelly Gang),这部电影改编自一群澳大利亚亡命之徒的真实故事,于 1906 年 12 月 26 日在墨尔本的 Athenaeum Hall 上映,一度引发骚乱。一天后,世界上第一篇影评诞生。Ryan 找到了墨尔本报纸《The Age》的数字存档,原文如下:
看得出来,剧组花了许多精力,非常认真地还原了惨剧发生的经过,就算有什么瑕疵,影厅里的观众也没有那么好的记性能记住。
这部电影在 Athenaeum 上映五周,场场爆满,随后又在悉尼上映。所以,Ryan 又查了悉尼的《Daily Telegraph》,找到了第二篇影评:
这部电影清晰明了,作为一部丛林片,主角的表现也相当突出。电影的拍摄地在“Kelly Country”,当然,拍摄获得了充分许可。这种影像加文字的记录毫不逊色于今天的现场拍摄。
这两篇文章在刊登 112 年后,被上传到了烂番茄。Ryan 将第一篇判定为“新鲜”,第二篇则是“烂”。在进一步发掘史料之前,甚至直到世界毁灭,互联网上关于《凯利帮的故事》的权威影评可能就只有这一个红番茄和一个被砸烂的绿番茄。
就是这么奇怪,在我们这个割裂的后把关人时代的文化中,最接近鉴赏权威的,居然是一个用卡通番茄评价电影的网站。由早期员工设计的烂番茄新鲜度,现在已经成为了影视领域的“好管家”认证。红就是好,绿就是坏。
新鲜度由一群专门的编辑管理,他们会阅读大量认证影评人的文章,判断哪一个是好评,哪一个是差评。当然,一部电影至少要五篇影评才能给分。
每一部电影的新鲜度等同于它的好评率。举个例子,John Travolta 2018 年的电影《高蒂传》新鲜度 0 分,就是说 55 位影评人的影评中没有一个被判定为好评。59 分以下是烂(绿番茄),60 分及以上是新鲜(红番茄)。
烂番茄的创始人说烂番茄这个名字来源于电影《里欧洛》,片中的小男孩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只浸染了某个西西里男人精液的番茄。不过这个名字更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人看到一出烂戏就往舞台扔水果的实践。基于这样的精神,烂番茄也提供了爆米花图标的观众评分,由观众给电影打分。
成立于 1998 年的烂番茄最初只是几个伯克利研究生给成龙电影打分的地方。但“给电影打分”这件事自带的商业价值促使烂番茄成为了一家有分量的公司。乔布斯在开发布会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提过烂番茄。从梅丽尔·斯特里普到马丁·斯科塞斯,这些好莱坞的精英们也会时不时提起烂番茄。对于那些想让你掏钱的电影公司而言,烂番茄是不可忽视的地方。
2010 年,烂番茄被 Flixster 收购,一年后 Flixster 又被华纳兄弟收购,2016 年 Flixster 的大部分股份又被华纳卖给了票务公司 Fandango。所以你能在 Fandango 的电影售票网站上看到每部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在 Google Play、DirecTV 或者 iTunes 这些烂番茄的合作伙伴上,也能看见评分。对于影视公司来说,烂番茄则是一个宣发工具,对电影评分的报道也成了常规新闻类别。
随着影响力渐长,烂番茄也遇到了许多非议。到了 2017 年,像《加勒比海盗》、《海滩游侠》这样的大片的制片人开始因为影片表现不佳而指责烂番茄故意给他们打低分。还有一些阴谋论认为,烂番茄和制片厂有交易。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烂番茄的编辑会被收买,但烂番茄的观众评分确实已经被玩坏了。在《黑豹》和《惊奇队长》上映时,一些男性漫画粉丝涌入烂番茄给这些电影刷低分,只是因为他们讨厌黑人和女性。
尽管如此,烂番茄的分数依旧有一种权威的诱惑力。作为一个用户,我条件反射般地相信,60 分的电影就是比 59 分的电影好。尽管这些分数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在选择无穷无尽的世界里,在逐渐被算法推荐接管的互联网上,烂番茄代表着某种更加古老的东西。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最好的选择方式是什么?或者更直接一点,你该相信谁?
“这篇算不算影评?”,这个问题烂番茄的编辑部每两周都要讨论一遍。这天我也在场,会议由在烂番茄任职 27 年的 Haña Lucero-Colin 主持。烂番茄和 Fandango 共用办公空间,内部挺有硅谷范儿的,你可以在墙上写东西,也能把墙拆了。隔间、卡座、角落,橙色的 Fandango 图标随处可见。不过开他们会的状态不太像创业公司,更像新闻学院的研讨会。
他们的讨论会一般这样进行:编辑拿出一篇文章,所有人判断它到底算不算影评。就这么简单。烂番茄不会考虑专题报道、推特的推文和影片概述。这次讨论会包括一篇《卫报》关于《30 Rock》过于依赖明星客串的文章,一段关于文化类播客的讨论,以及一篇刊登于《Entertainment Weekly》关于晨间真人秀节目《The Bonnie Hunt Show》的文章。这些推进得都非常迅速,全都不算影评。
那天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编辑 Robert Fowler 提出的,《纽约》杂志网站 Vulture 上刊载的一篇关于《Nancy Drew》的文章,作者是 Matt Zoller Seitz。在 Fowler 看来,Matt Zoller 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借这部电视剧谈谈电视的本质,这是他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影评只是这位电视评论家的副产品。”Lucero-Colin 同意这一观点。那么这篇文章到底算不算影评呢?没人能下结论。最后:Lucero-Colin 给 Zoller Seitz 发了一封邮件。后者回复:“好评。”
像这样的讨论会对保持新鲜度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对此没有人比 Jeff Giles 理解得更深刻。作为一名远程工作的新罕布尔州居民,Giles 从 2005 年开始为烂番茄做编辑,自那时起,他也自己做了一个流行文化网站,并为肥皂剧写了一本 381 页的口述史《One Life to Live》。
Giles 也会不定期到佛利山办公,来到这里后他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每一位编辑都要追踪几本出版物。Giles 作为管理者,主要负责《纽约客》、《纽约时报》这类 A 级刊物的评论家。工作内容就是评判一篇影评是好评还是差评,然后摘录一段合适的文字放在网站上。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是《Hollywood Reporter》关于《The Wayfarers》的影评,写得弯弯绕绕,难以判断。好在文章开头有个摘要帮 Giles 做了判断“缓慢的开头变成了深深的感动”——是好评。随后,我们又仔细阅读了清晰明了的《Springtime for Nazis: How the Satire of 〈Jojo Rabbit〉Backfires》,原载于纽约时报,作者 Richard Brody。
我觉得不过瘾,于是 Giles 给我发了一篇充满优越感但又轻松幽默的《唐顿庄园》电影版影评。这篇他已经看过,作者是《纽约客》的 Anthony Lane“作者似乎觉得这部电影不应该存在”,他评价说,“但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并不痛苦,你知道吗?”记住:烂番茄没有明确的好坏标准,也没有必须完成多少篇好/差评的指标,只有编辑的判断。这篇影评比较矛盾,但我倾向于好评。Giles 表示赞同:“我们把这种叫‘绅士的好评’。”但他似乎忘记了他对这篇影评的判断:差评。我问了一下 Giles 最喜欢什么样的影评人,“观点清晰明了的”,他说。对于那些喜欢用字母打分的媒体影评,Giles 给出好评的标准是 B-及以上。
干这行速度也很重要。刚刚在烂番茄工作一年的 Kristin Livingstone 说,编辑们会把观点暧昧的文章扔进工作群,“有些编辑会很快回复是好评还是差评,”她说。
编辑们一天要判至少 50 篇影评,这个节奏容不下多少揣摩时间,尤其是现在烂番茄还引入了 YouTube 和播客影评。每周的影评完成数量都集中在一个共享的表格里,“就像比赛积分榜一样。”每周的达标额度是 200 篇,不过没有完成也不会有惩罚。
烂番茄也在尝试解决工作量的问题,影评人现在可以自己上传并判定影评。现在,这类影评大约占 30%,不过我能感觉到很多影评人希望烂番茄新鲜度不存在。《时代》影评人 Stephanie Zacharek 就抱怨过这种非好即坏的判定方法无法处理“一部好看的烂片”这种情况。现在大部分的影评人都不会在写影评的时候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烂番茄新鲜度现在被“流行主义”(认为商业文化产品也值得被严肃批评)扭曲了。“90 年代的电视评论都是相当刻薄的”Lucero-Colin 说,“每一篇影评看起来都像‘这节目就是屎,我们不会再看第二遍了。’现在的电视评论说教意味很浓,就像‘嗯,他们干得不错,但不够好,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明星的。’”
此外,由于新鲜度这个评价没有区分完全好评和“绅士的好评”,所以爆米花电影和严肃经典的分数往往差不多。例如《蜘蛛侠:平行宇宙》新鲜度 97%,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新鲜度 95%。据分析,每年烂番茄新鲜度的平均分都在变高。
“因为所有东西都被抽象成了好或者坏。”前烂番茄编辑 Matt Atchity 说。“正是这种极端的数字让烂番茄一直流行,一直出现在新闻报道里。”
回到《凯利帮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第一篇影评是好评,确实没有说这部电影的什么缺点,但“花了很多力气”和“认真”也算不上什么溢美之词。第二篇影评开篇就说,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犯罪电影算不上对澳大利亚价值观的大肆宣扬。虽然是差评,但影评人并未批评电影本身,相反,字里行间还有一种这电影拍得还行的意思。问题不是 Ryan 错判了影评,换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问题是烂番茄的世界里只有“新鲜番茄”和“烂番茄”,没有“生番茄”和“熟番茄”。
Giles 最近收到了一个来自影评人的投诉,她反对烂番茄将她的影评算作好评。“她说,‘我真的不喜欢那部电影。能换成差评吗?’我说,‘当然可以,但我想问问,为什么你要给 B-?’她的回答很简单,‘我讨厌打分,就随便给了一个。’”Giles 后来又补充说,“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
在采访的第二天,我和烂番茄的一线采编人员吃午餐,他们和影评编辑不一样,主要采访电影明星、参加电影节。我问他们,作为烂番茄的一份子,他们是否认为外界真正了解烂番茄。答案是否定的。编辑 Jacqueline Coley 说,她从来不告诉 Uber 司机自己真实的工作,这样对方就不会问及她无法控制的电影分数。她也听有些人抱怨评分算法,但 Coley 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算法。”
确实没有,否则刷分这种事就不会伤及烂番茄了。两年前《星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映时,观众评分跌倒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现在是观众评分 43,烂番茄新鲜度 91),导致用户怀疑烂番茄新鲜度是不是被收买了,还是又发生了一出恶意刷低分闹剧。
失去了评分公正的信誉,烂番茄什么都不是。为了建立信心,烂番茄解决了这个问题:影片上映前不允许用户打分,同时要求打分用户验证电影票。
观众评分规则变动的同时,新鲜度的规则也迎来了大改。在 2018 年 8 月之前,只有几家出版机构的影评人才能入选烂番茄新鲜度评分,这些人大部分是白人、男人、老人。现在,有 600 名新影评人入选,其中大部分是自由影评人,且多为女性。不过当影评人队伍扩大到了 4500 人这个规模,就难免会出混进一些滥竽充数的人。几年前,一个叫 Cole Smithey 的影评人就为了破坏《伯德小姐》的 100% 好评给了一个差评。
我们很难弄清楚烂番茄的评分对电影票房有什么影响。在 2018 年末,Morning Consult 举行了一次全民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看电影前查一下烂番茄,有 63% 的人会因差评选择放弃观看。但不管有没有影响,对于好莱坞来说都要争取。所以制片厂会在临近上映时才给影评人举行放映会,遇到差评,会向 Giles 这样的编辑表示抗议。
“我也注意到了‘新鲜’对于制片厂和制片人而言非常重要,”他说。如果一部电影新鲜度在 75% 以上,并且参考影评超过 40 篇,就会有一个“烂番茄认证”的小标签。“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在宣发中的价值。”美国最大的连锁影院 AMC 会在官网上显示电影的烂番茄新鲜度,但只显示有“烂番茄认证”的。
卖电影票的 Fandango 买下烂番茄也不是为了让观众少看烂片。为了完全掌控烂番茄,烂番茄没有负责人,由 Fandango 的总经理 Paul Yanover 直接管理。不显年龄的长相和程序员背景让他看起来不像个精明的商人,但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实际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很有用的宣发平台。”他对我说。
Fandango 的盈利方式有几种。一种是观众通过他们的平台买票,能收一笔“过路费”。另一个是向内容供应商(前面提到的 iTunes、Google Play 等)授权,允许他们使用烂番茄评分。
“显然,烂番茄有极高的自主性,”Yanover 说,“不过 Fandango 作为一个售票平台,也一样。”在他看来,烂番茄和 Fandango 的使命是一样的:把你会喜欢的内容送到你面前。
Netflix 的算法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唯一的区别是,Netflix 比影评人更了解你的喜好,甚至比你自己更懂你。但 Netflix 不会显示烂番茄新鲜度,实际上 Netflix 上什么评分都没有。相反,他们是根据你过往的观看历史向你推荐电影。Spotify 的歌单,Facebook 的信息流也是同样的原理。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周围充斥着被算法推荐的内容。
烂番茄新鲜度有这么多缺陷,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他?**因为当 Netflix 想用算法把你永远留下时,烂番茄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让你离开它。**你会经他的推荐去看一部电影,或是拒绝一部烂片,但这一切行为都源于你的自由意志。
“在烂番茄,有一些用户有自己喜欢并信任的影评人,”《时代》影评人 Zacharek 说,“他们会点开链接看影评。”如果使用得当,烂番茄其实是一种无尽的资源,就像互联网最开始时那样。
现在,Tim Ryan 的电影档案计划已经为 210 部老电影创建了页面,收集了 5500 篇影评,没有烂番茄,这些影评和写它的人大部分会被埋没在历史资料里。
题图来自《连线》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