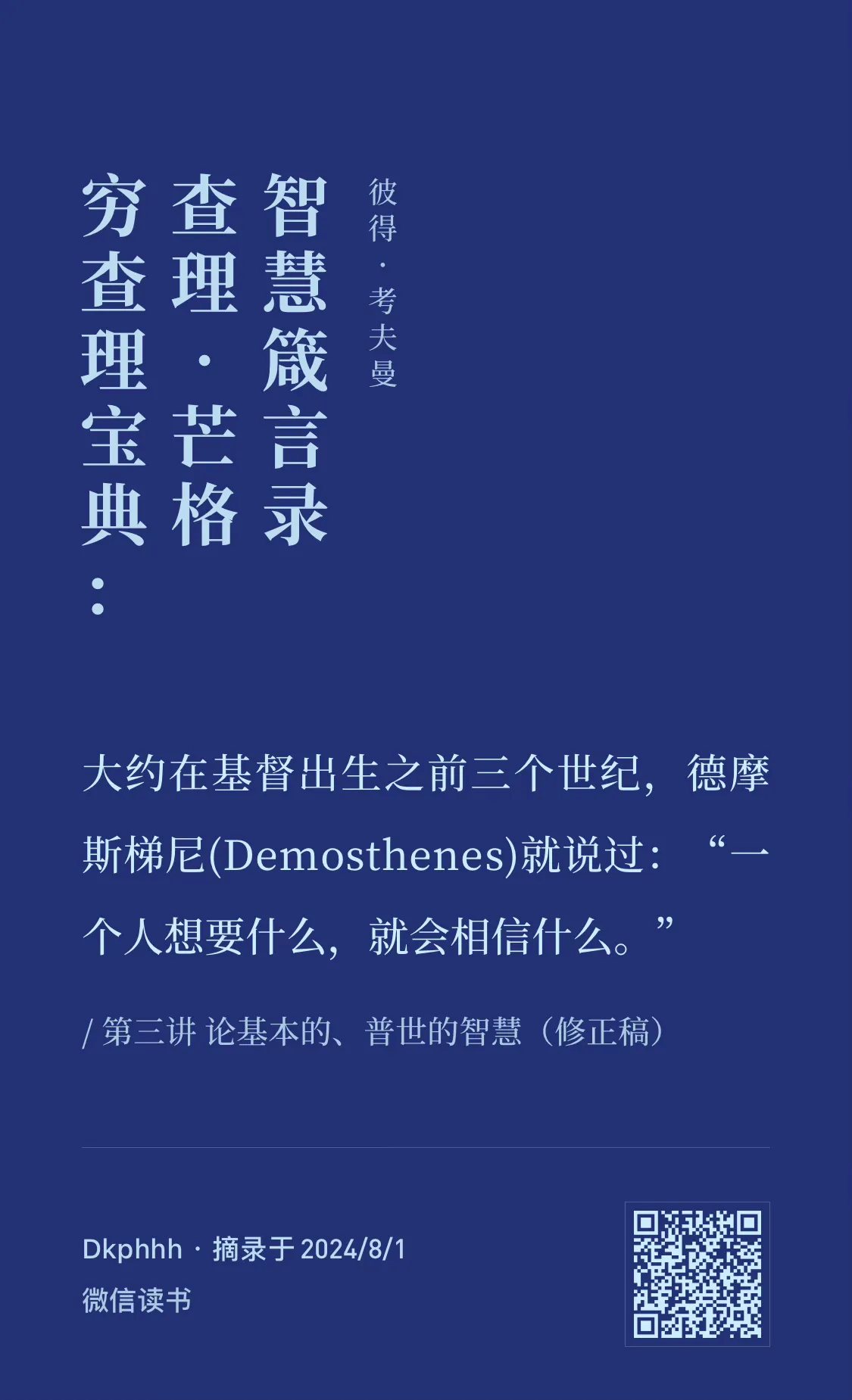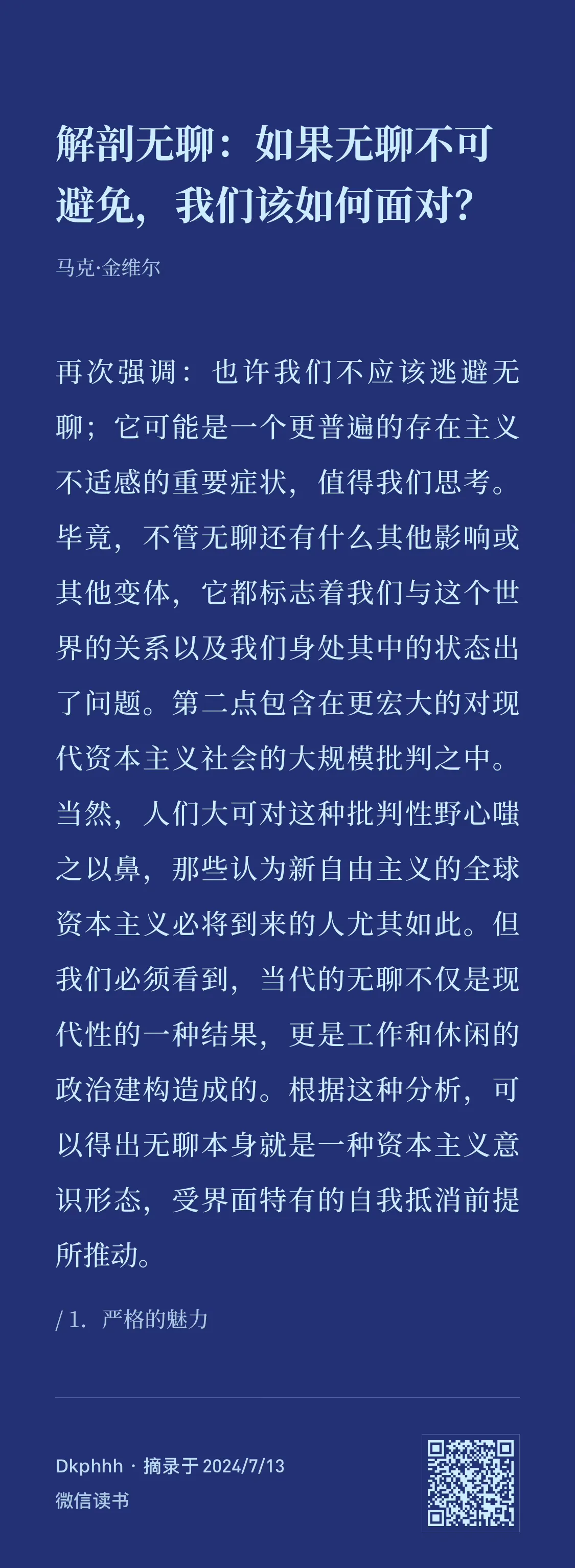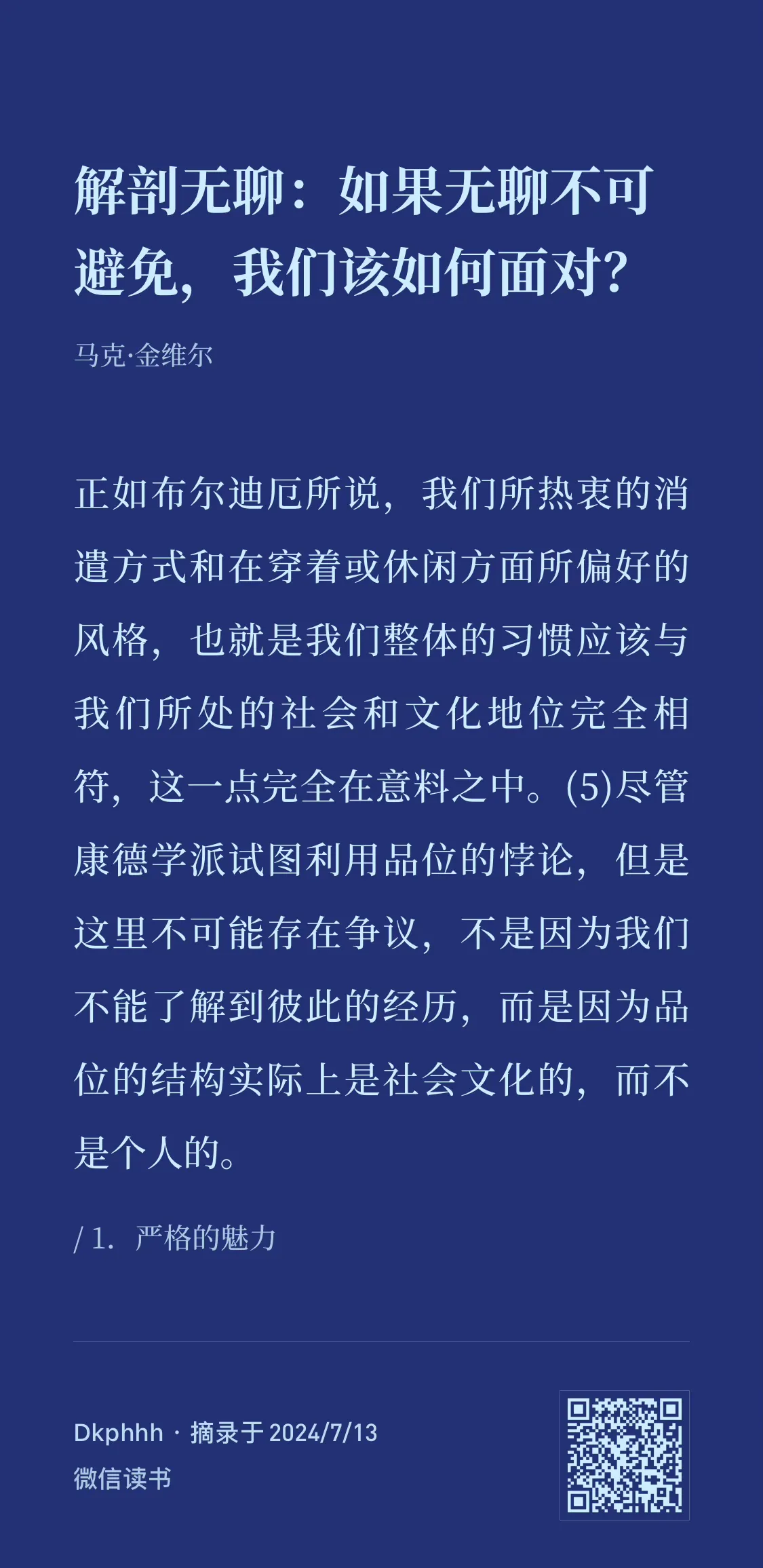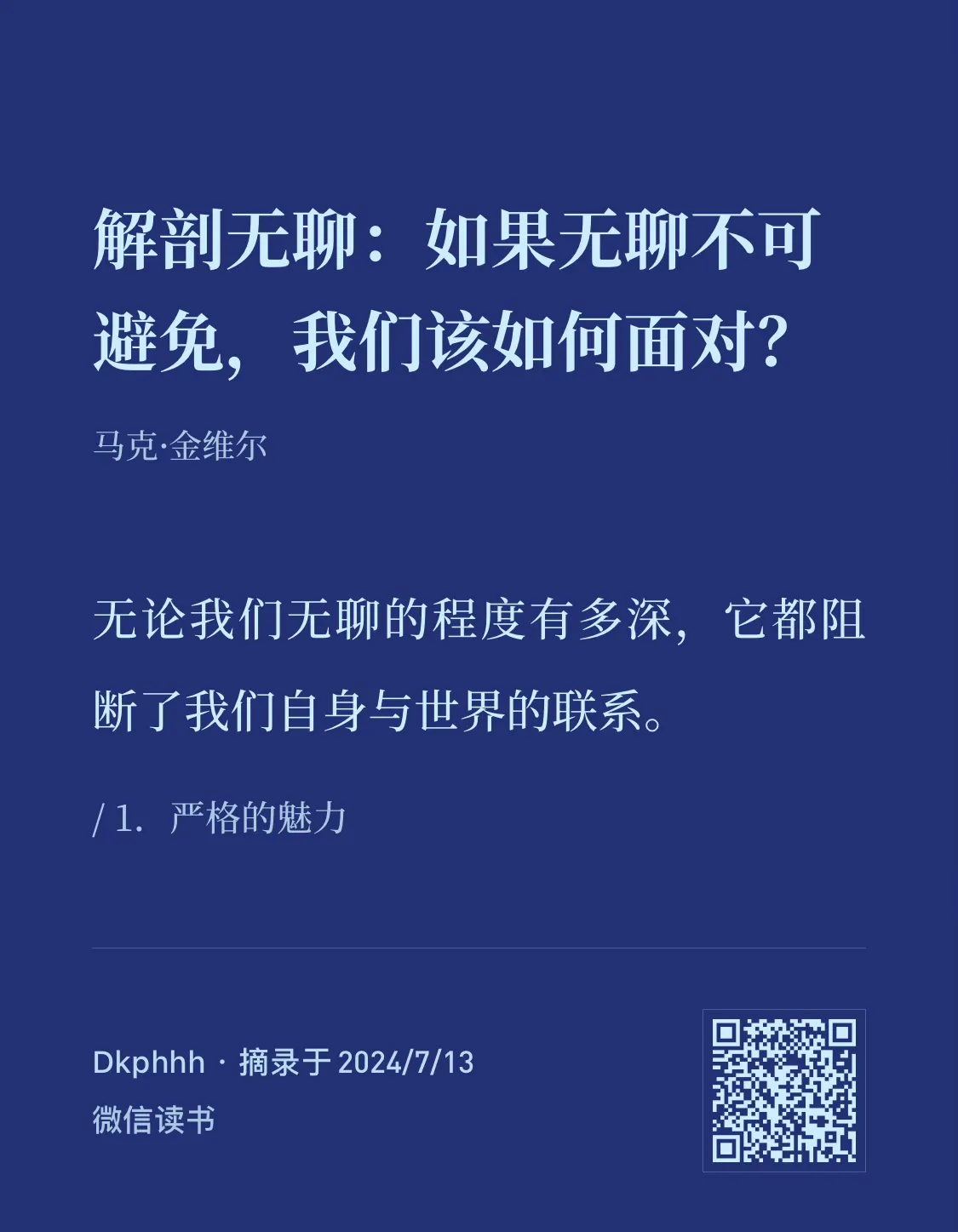张潇雨谈如何确定自己喜欢做的事
没事儿做点思想实验挺好的,刚才临时起意出了一个,可以玩一玩。 还有另外一组我觉得很经典的思想实验,之前在播客里也录过一期节目,是关于“如何判断自己喜不喜欢做一件事的”。描述如下:
- 如果此刻就把做这件事的附带结果都给你,你还愿意继续做它吗?比如你正在为了减肥 20 斤跑步,但如果现在立刻你就能比较健康地瘦 20 斤,你还愿意跑步吗?
- 如果有一件事你只能默默做,不能告诉任何人,你还愿意做它吗?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 假设你有两件喜欢的事,A 和 B。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外星人说,它可以给你提供无限的资源,在你剩下的人生里慢慢帮助你把 A 做好,但前提是你这辈子再也不能做 B 了。你愿不愿意答应它?
- 最后,如果你注定十年后的今天会死掉,那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吗? 人生未来好几十年,都可以时不时拿出这几个问题来问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