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对自我最彻底的消耗方式是对(我们想象中的)目的的追求。因为自我和它所相信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借由科技的助推,并且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很难厘清这些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普通的技术条件促成的。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当面对似乎不可避免的现实时,我们究竟能集中多少政治资源和个人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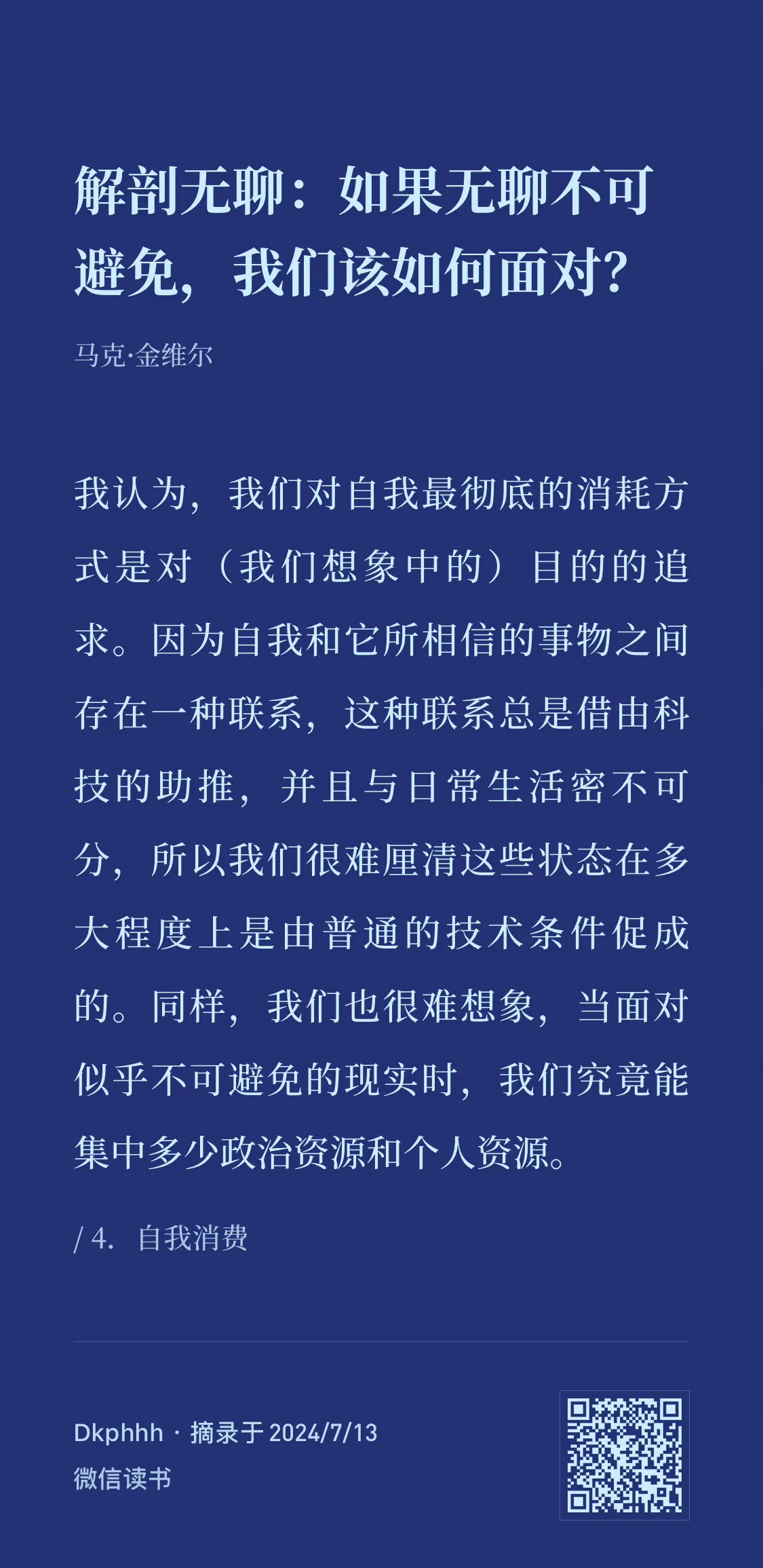
我认为,我们对自我最彻底的消耗方式是对(我们想象中的)目的的追求。因为自我和它所相信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借由科技的助推,并且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很难厘清这些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普通的技术条件促成的。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当面对似乎不可避免的现实时,我们究竟能集中多少政治资源和个人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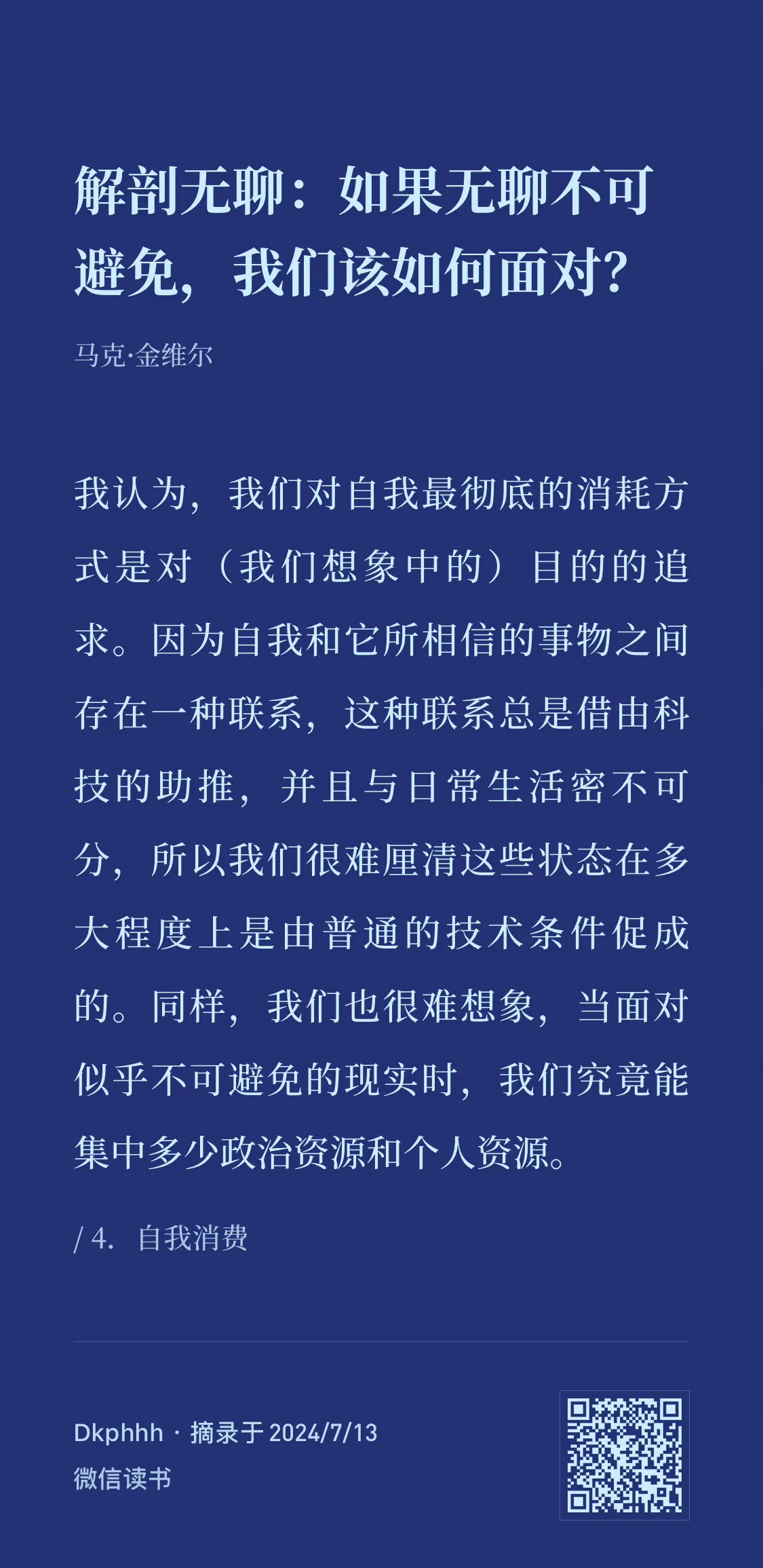
科技以“座架”(Ge-stell)的形式,展示了它创造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意味着它能让所有东西变得可获取并且可任意处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储备资源”的森林被视为潜在的木材,瀑布被视为潜在的水力发电的资源。
但是我们绝不能认为座架效应,即将世界重新定位为一种储备资源,并不会涉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资源,可以作为更大规模的可处理的元素来生产和消费。我们是用来工作的商品,就像“人力资源”这个用语所传达的,这些工作环境声称会在难以察觉的商品化迹象下保护我们。更严重的是,我们是满足自己欲望和愉悦的消耗品,让“自我”这个概念变成了一种可以像电子游戏或网飞视频一样被获取的产品。事实上,由于我们自身的人格存在常常缺乏与商业产品相关的结构,因此我们甚至可能渴望达到这种被描述为经典的产品所呈现的“连贯性”水平。我们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制作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东西一样得到精心策划并被分享,好让某位无聊的观众在随意浏览各种信息时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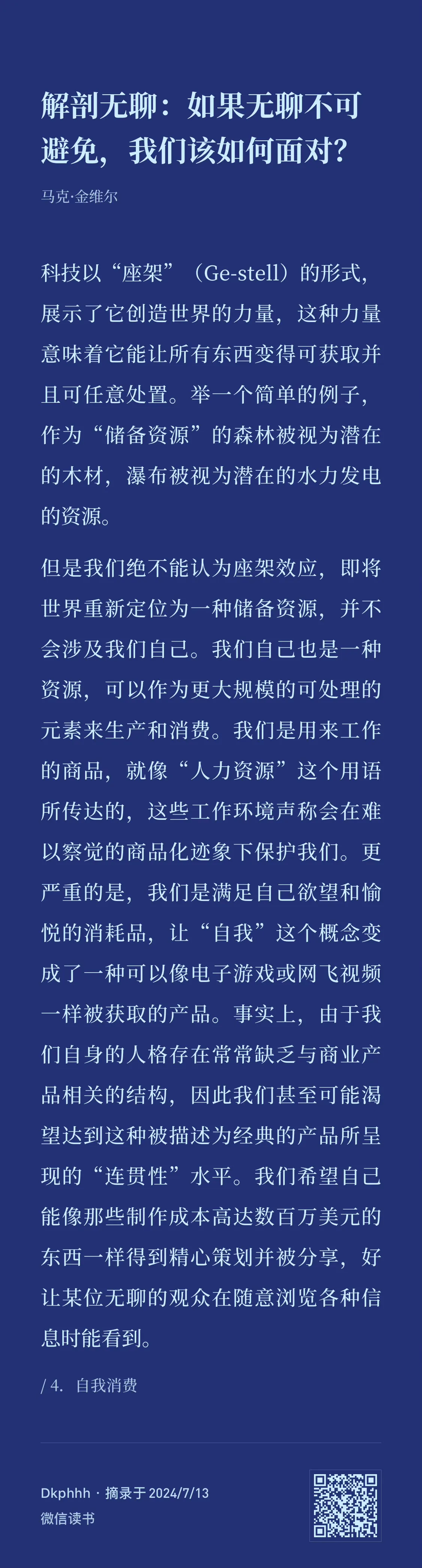
如果一款游戏被称作是“高度上瘾”,也就意味着它短期内会一再延缓人们抗拒沉迷和刺激的理智心态。这是新自由主义无聊的核心,它所诱导和加剧的症状正是原先它承诺要缓解的症状。我们完全出于自愿,甚至热情参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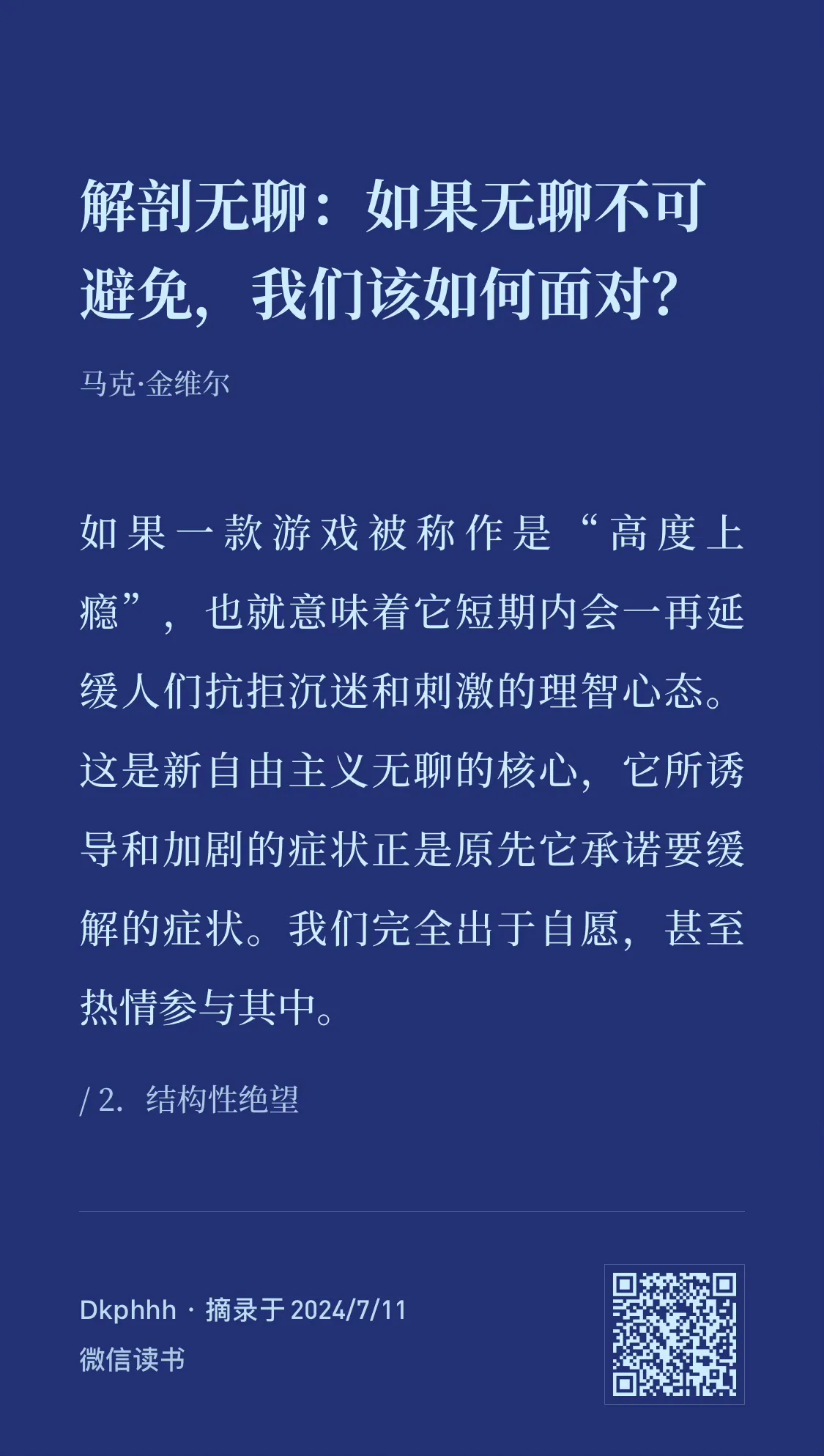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家族财产似乎会神奇地让财产的受益人觉得自己的政治或美学观点应该受到格外尊重。
“挣来的”而非“继承来的”财富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往往会掩盖使其产生的市场基础——那些自己创造财富的人认为,和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却以为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所致的人相比,他们所赚得的财富要名正言顺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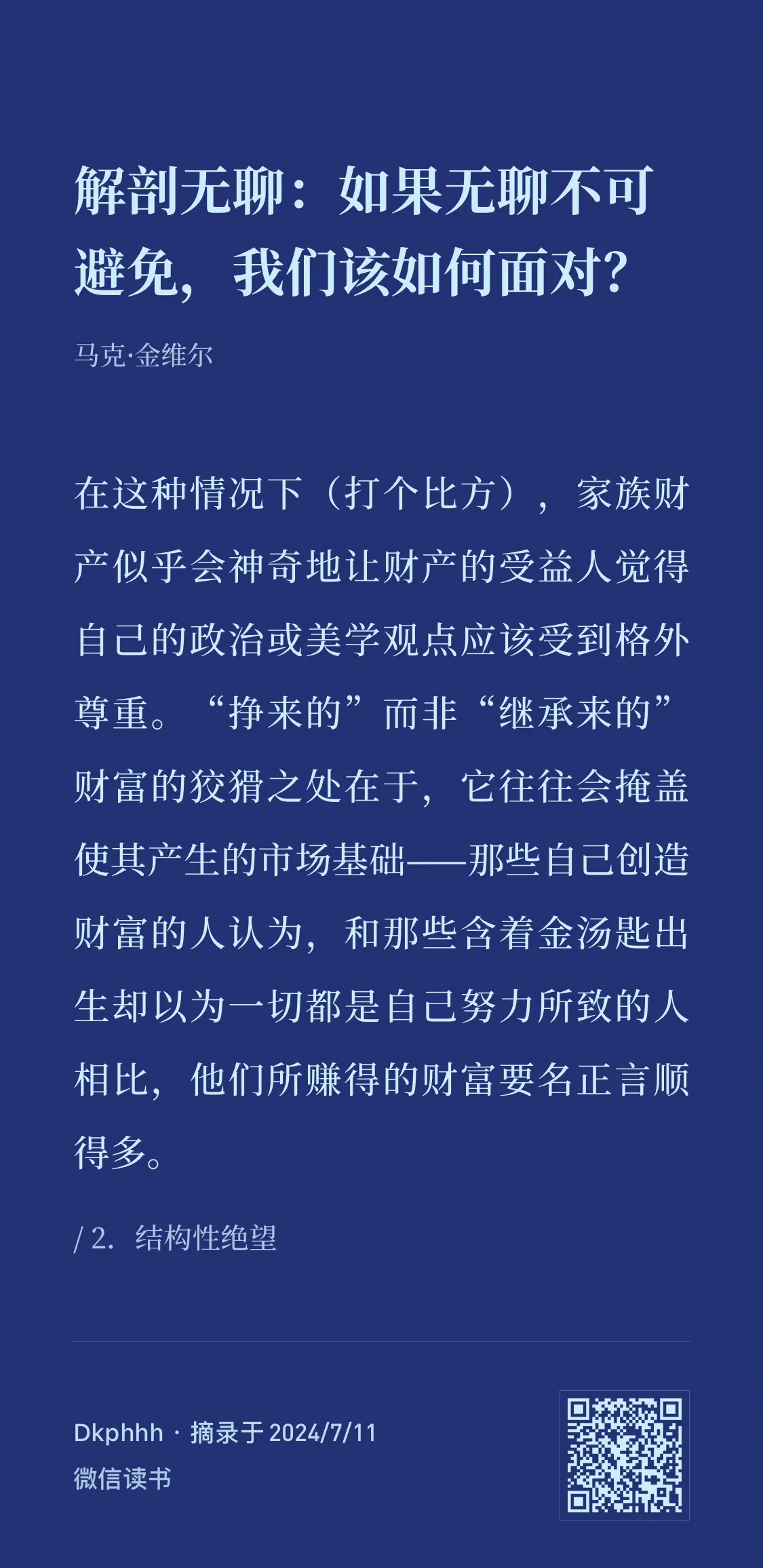
贫穷和苦难不是错觉,也不是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小故障,而是其固有逻辑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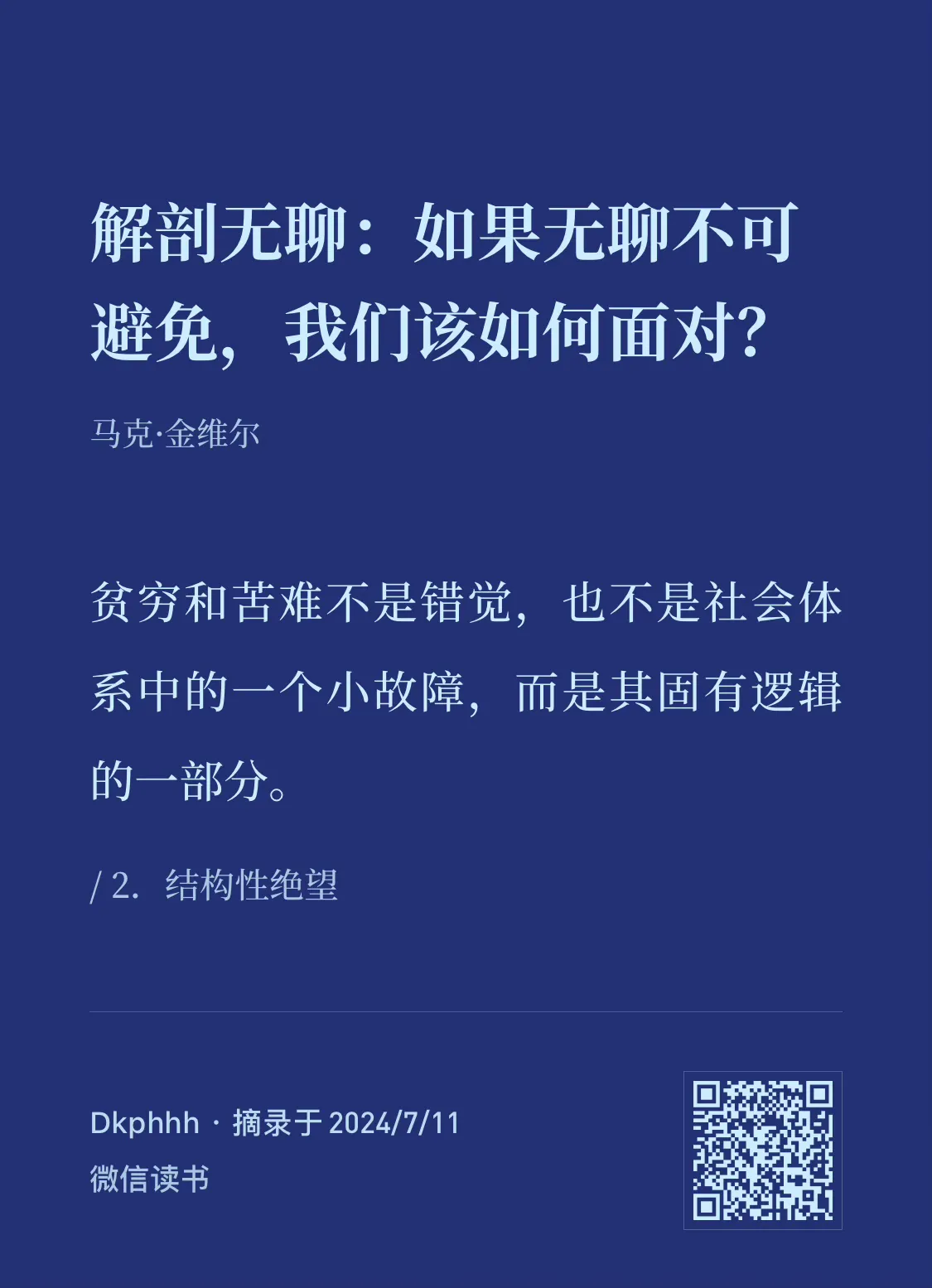
我们不是在见证历史,我们普通人是在承受历史。
我们不是在见证历史。正如 1957 年加缪所说的,我们普通人是在承受历史。他说作家(艺术家也同样)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
“很多人认为他们在思考,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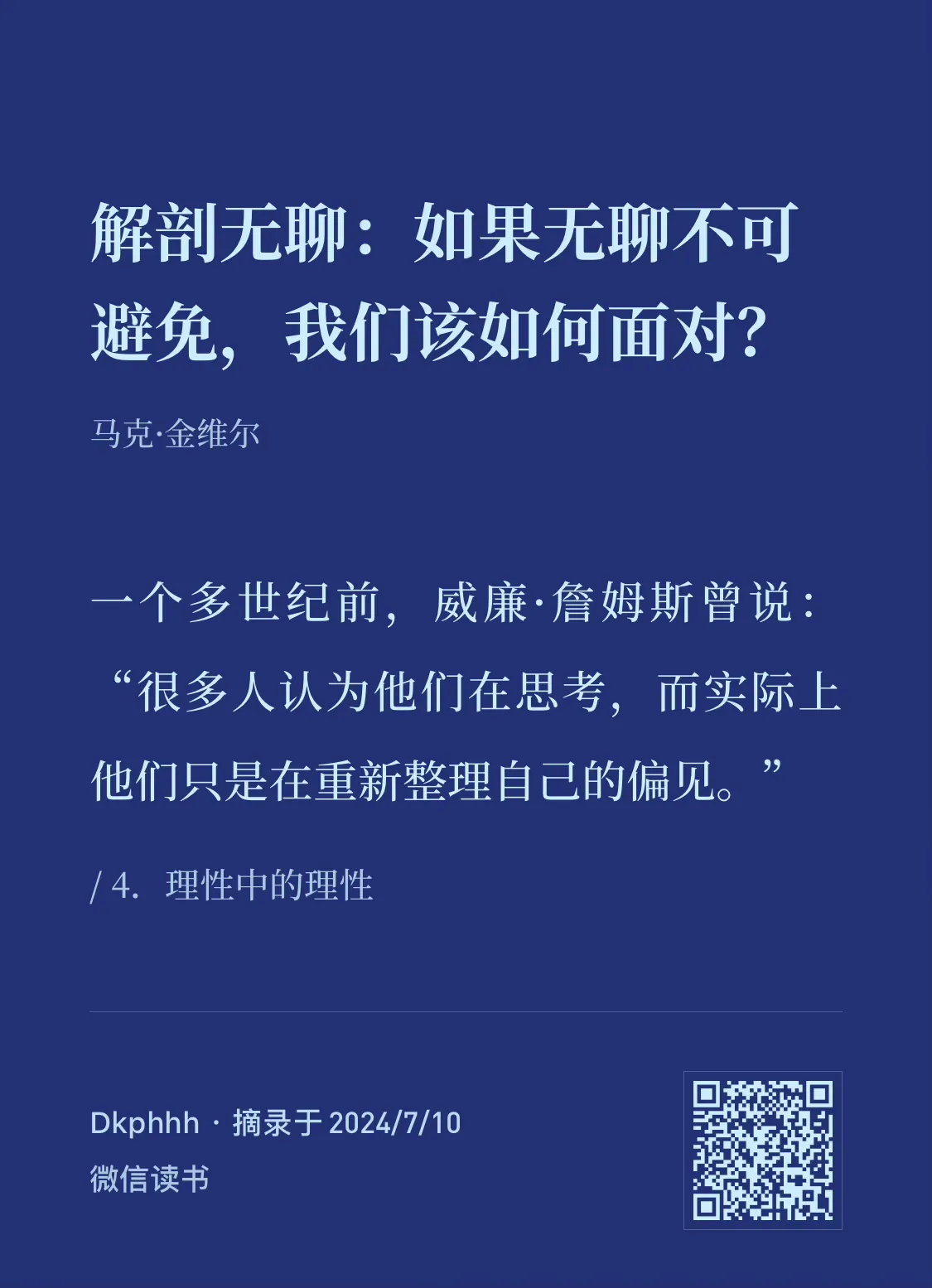
许多评论家认为,改变思维的方式比我所认为的要多得多——毕竟,人们很容易被说服,只要我们循循善诱,他们就能领悟。但这带有一种过时的智力优越感,伴随着一种浓厚的屈尊俯就的意味:我觉得你的政治观点冒犯了我,我猜想它们来自糟糕的、错误的或丑陋的基本信念。这些是可以改变的!让我把你放入我的话语疗法程序中,在这个程序里,我们会用善意、同理心和同情心对你的基本世界观进行批判,从而打破你的底层(双关)思维结构,最终你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更善良、更宽容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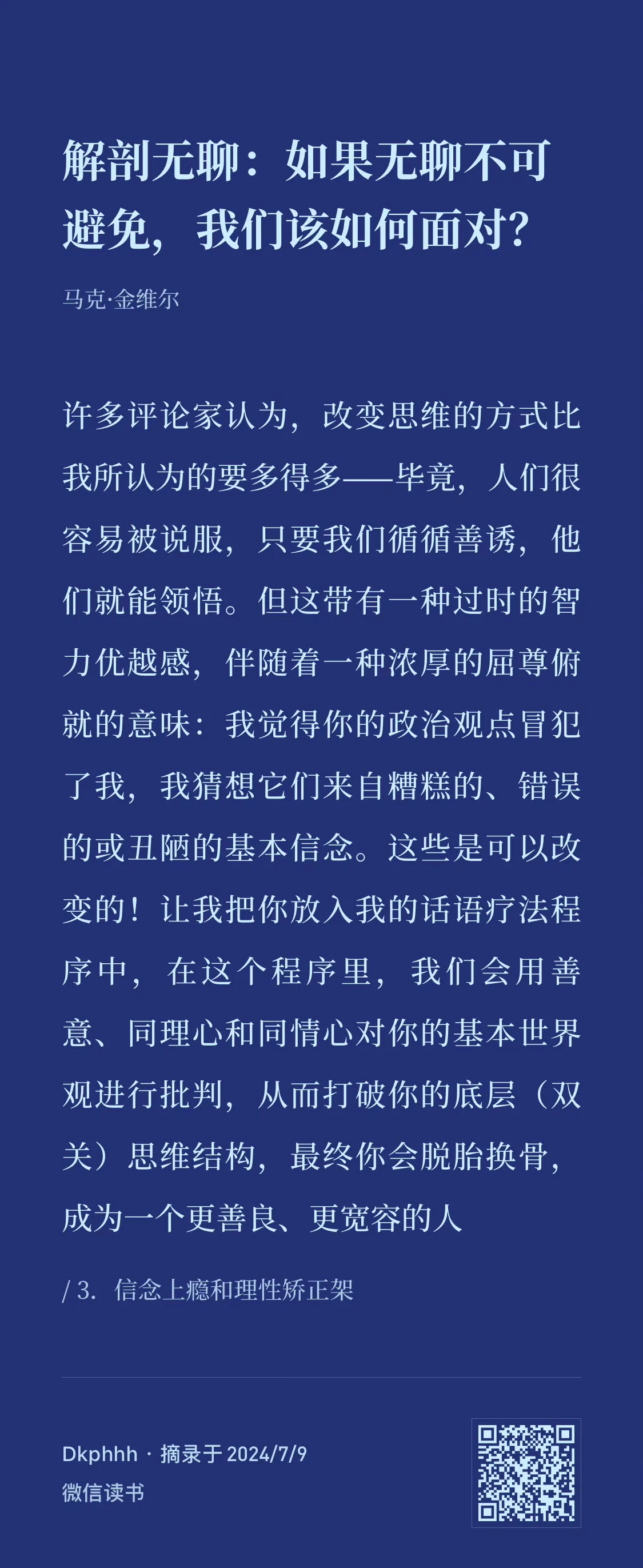
因此,我们要同样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信念上瘾的特质,不要再幻想公共言论自由会在没有监管和其他形式的话语限制的情况下向理性倾斜。在某些情况下,言论限制和严格的互动规则可能是正确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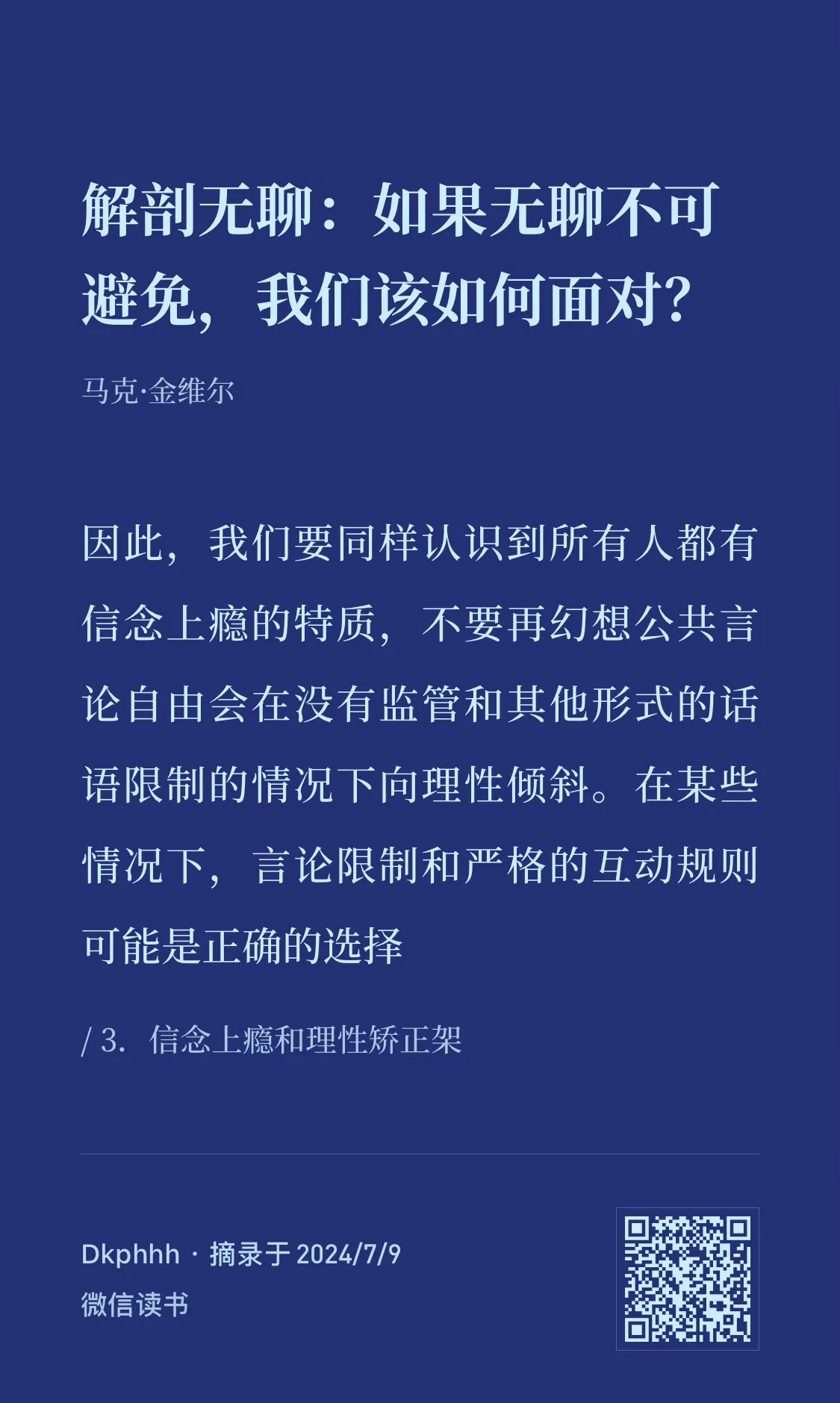
Claude 觉得自己是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