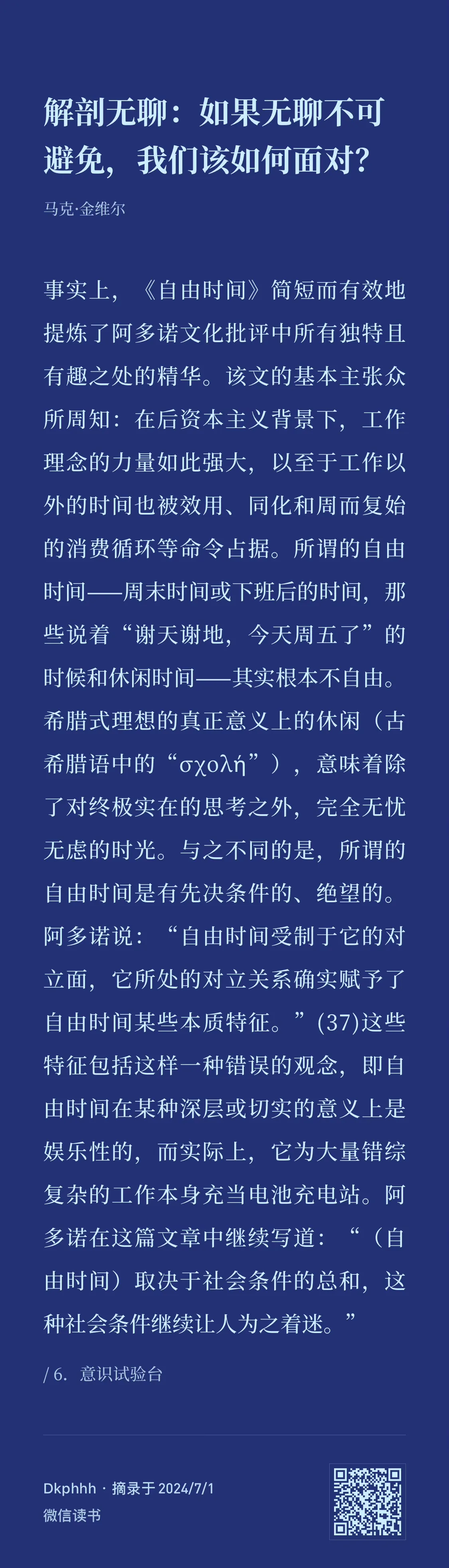今日职场吐槽:老板给了我两份文件,标题正文都列好了,让我去公众号排版。排完版以后,质疑我标题为什么这样写。我内心 OS:这不是你自己写的标题吗?
Tag: 生活
Dkphhh's MurmurCreated@ Tue Jul 23 2024 10:51: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Dkphhh's MurmurCreated@ Sun Jul 21 2024 17:22: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你需要为这个故事创造自己的版本,在这个过程里,这个故事成为了你的一部分。 说书人在故事里留下自己的痕迹,就像陶器制作者手掌的形状与纹路在陶器上留下的痕迹。
从这个角度看,制作陶器真的是一件非常感性的事。
Dkphhh's MurmurCreated@ Mon Jul 15 2024 19:45: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我是来放假的,不是来上班的。
Dkphhh's MurmurCreated@ Sat Jul 13 2024 05:51: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我认为,我们对自我最彻底的消耗方式是对(我们想象中的)目的的追求。因为自我和它所相信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总是借由科技的助推,并且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很难厘清这些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普通的技术条件促成的。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当面对似乎不可避免的现实时,我们究竟能集中多少政治资源和个人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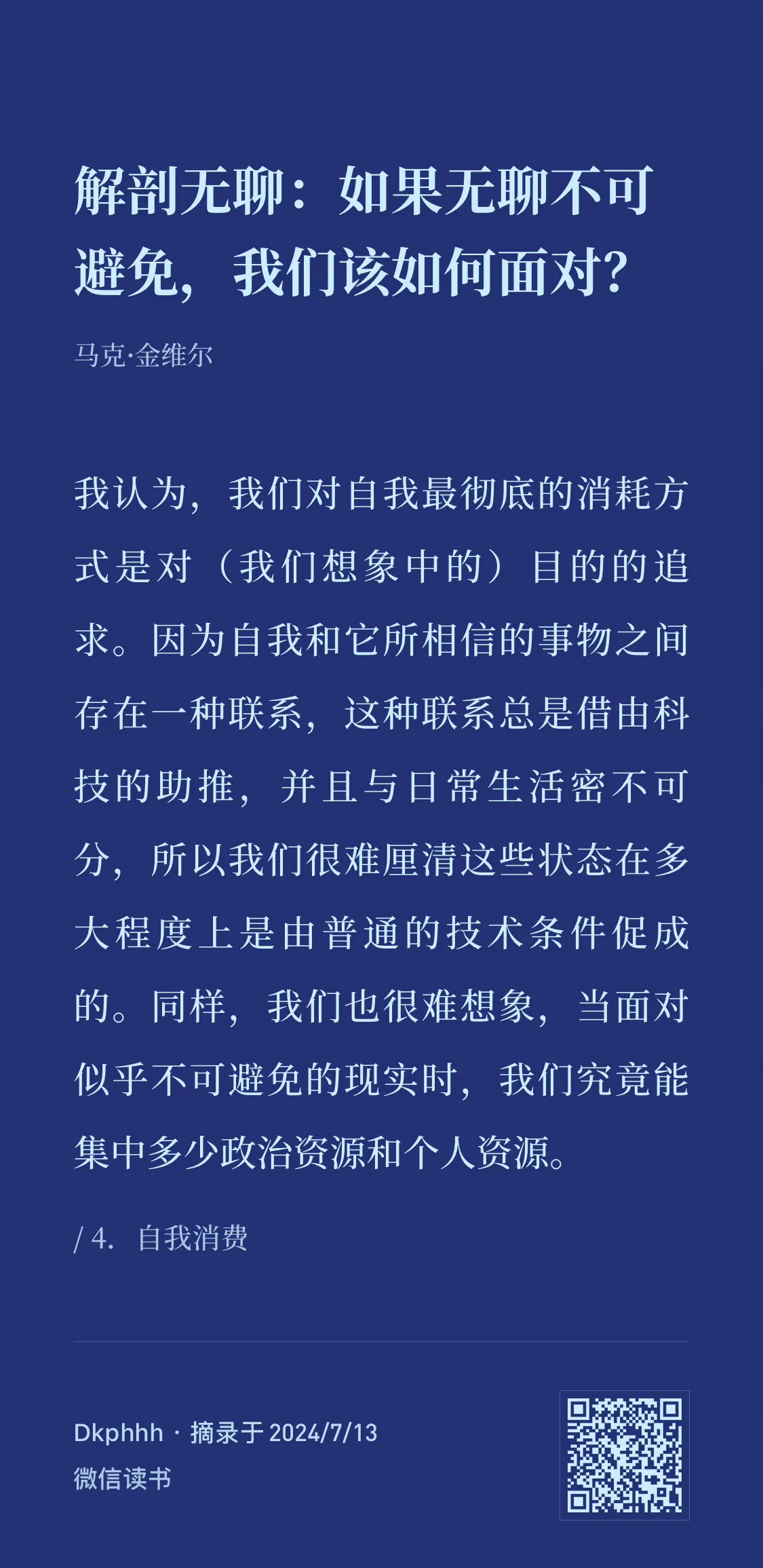
Dkphhh's MurmurCreated@ Wed Jul 03 2024 07:29: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休闲时间要么被同化为工作时间,呈现为工作场所里的“娱乐”元素(放映室、游乐室、休闲的着装规范、宠物收容处等),要么本身已成为劳作和竞争的场所。有时,这两种形式还会同时上演。因此,现代工作一族习以为常的一轮接一轮的周末狂欢表明,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工作的全面束缚。因此,当代休闲时间的无聊感是更深层次的精神萎靡的外现。当个体切换至工作自我时,这种萎靡感就会下降。根据这种分析,无聊是政治性的,因其投射出在劳动和自我的配置中一切都不顺利之感,个体无望地拘滞于罗网——我在其他作品中称为“工作理念”(the work idea)——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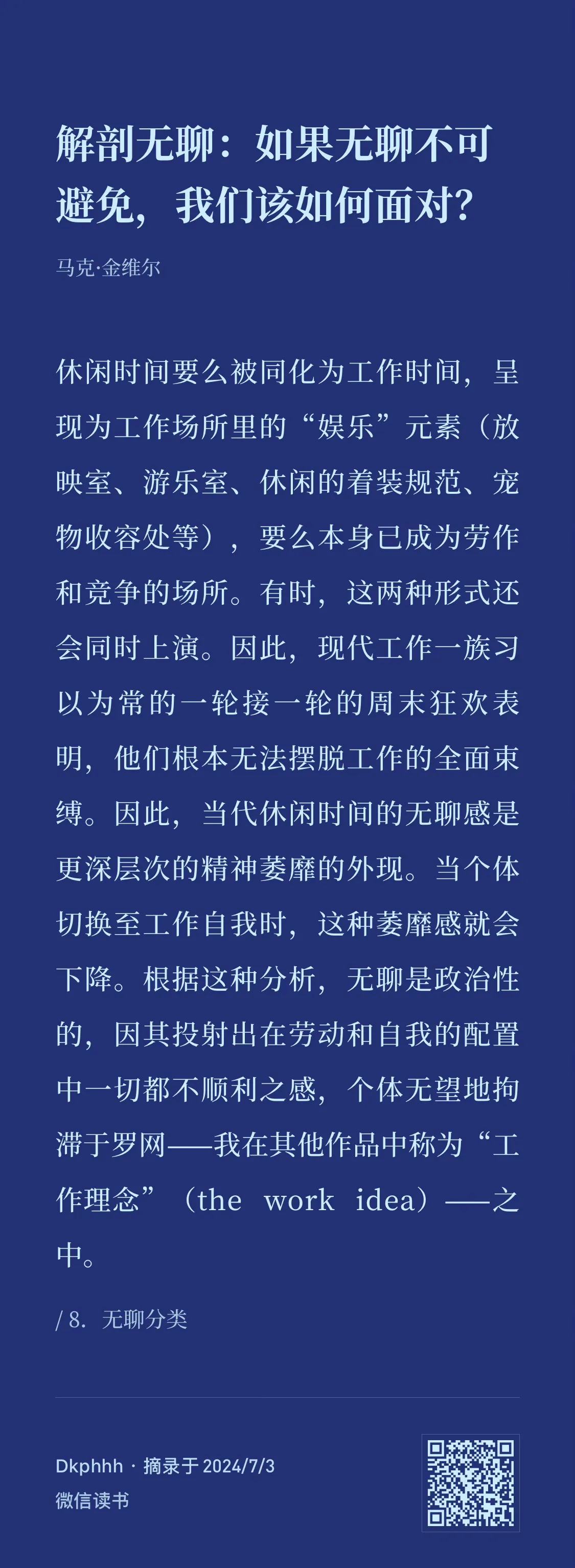
Dkphhh's MurmurCreated@ Tue Jul 02 2024 07:51: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无聊或许是当代人生活的基本特征,因为它标志着自我因如何得到满足而困惑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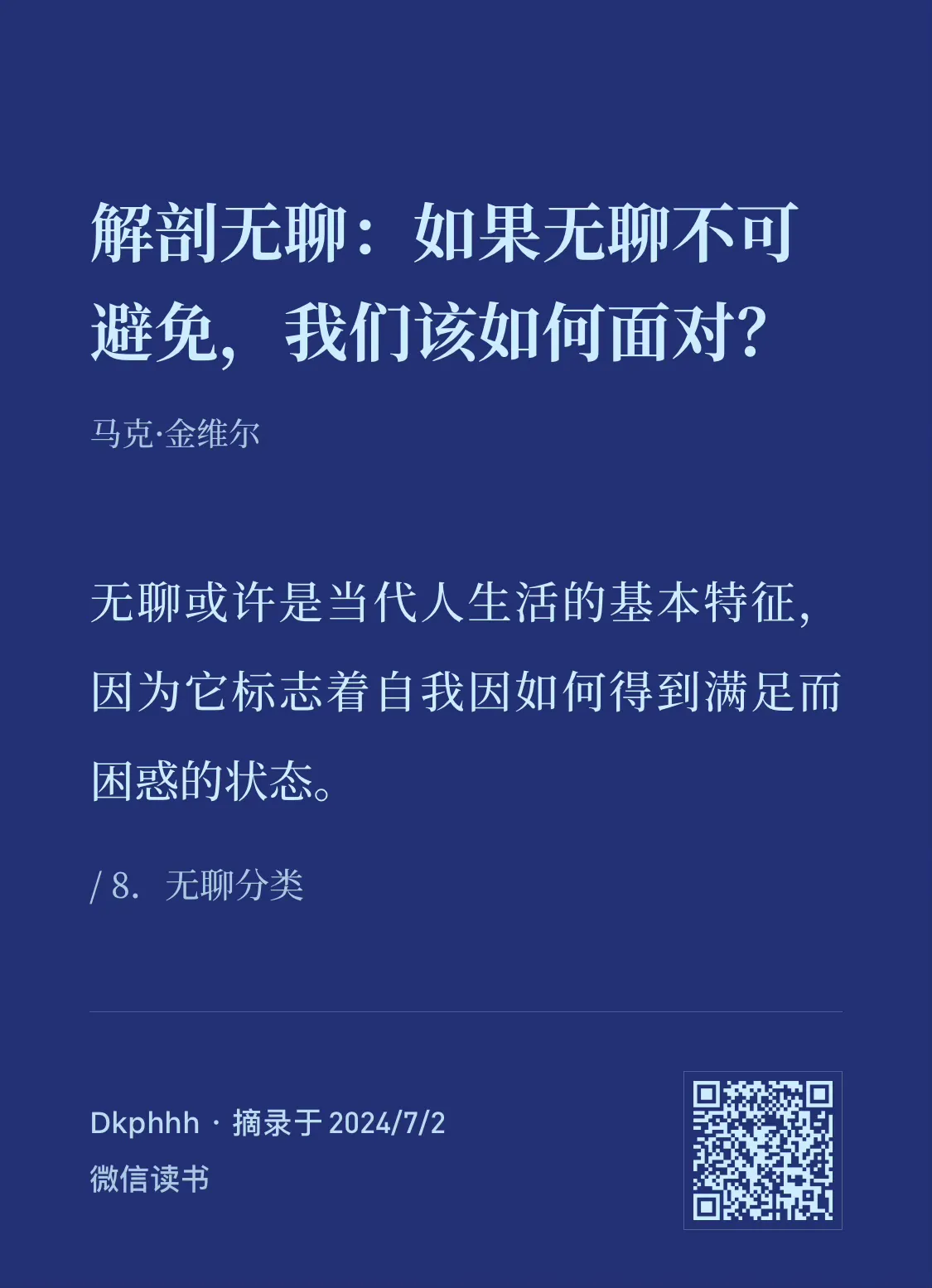
Dkphhh's MurmurCreated@ Mon Jul 01 2024 23:28: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自相矛盾的是,无聊其实也是我们行动的动力或催化剂。无聊可能会刺激我们去重新装修房子、培养一个新的爱好或找一份新的工作。这种感觉随即会激发人们去寻求挑战,而这就是矛盾的关键所在——许多人认为,无聊会让人变得无精打采,但实际上,它却会带来满满的活力,激励人们去寻求‘改变和丰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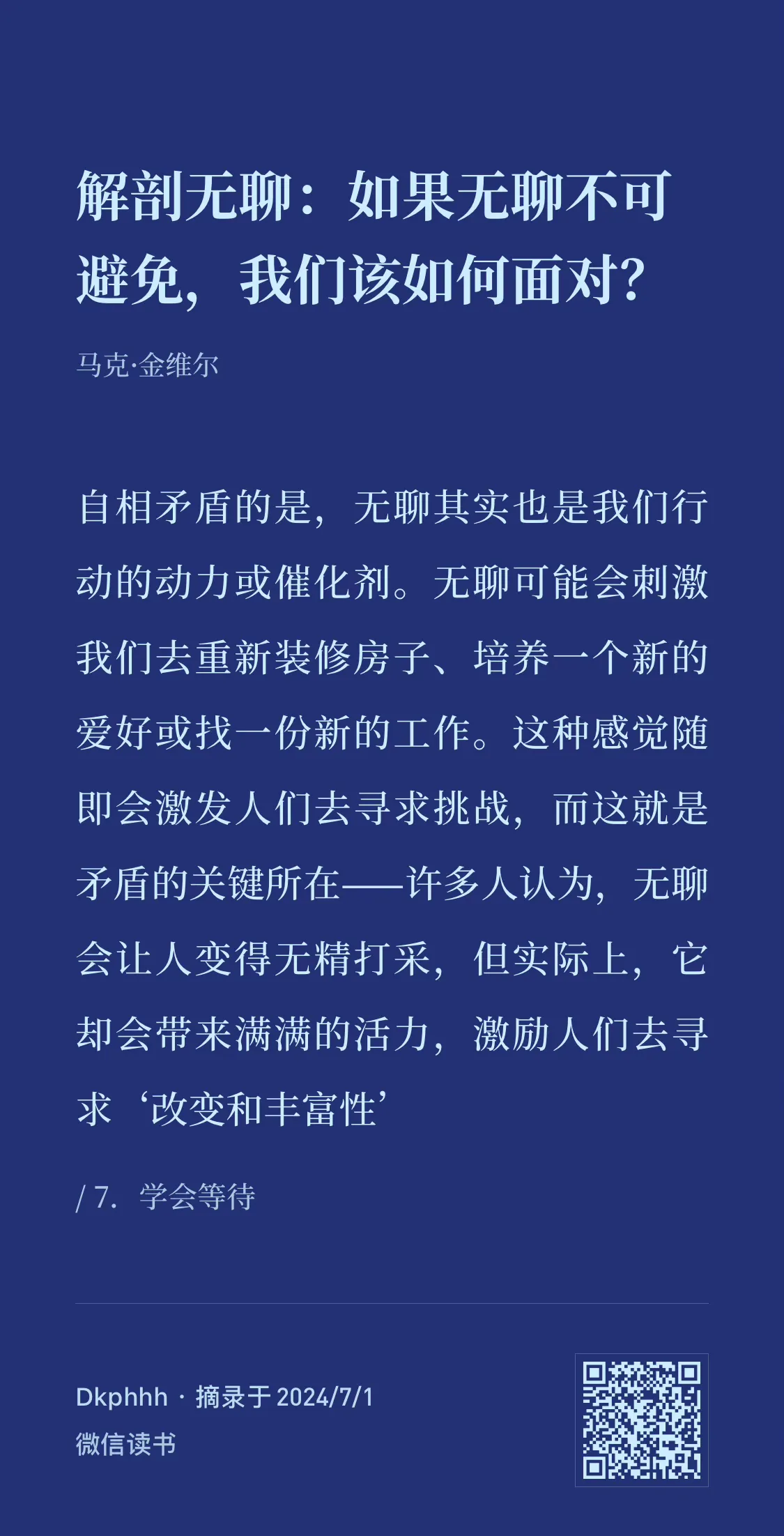
Dkphhh's MurmurCreated@ Mon Jul 01 2024 07:59: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自由时间”——阿多诺用讽刺的引号(我们现在称为“着重引号”)把这个短语括起来——“正逐渐趋向于其自身的对立面,并且正在成为对自身的一种嘲讽。因此,不自由正逐渐吞噬着‘自由时间’,而大多数不自由的人对这一过程并不知情,正如他们对不自由本身并不知情一样”。(39) 人们一旦察觉到这一点,扮演着劳动世界隐形管家的自由时间之束缚也许就会土崩瓦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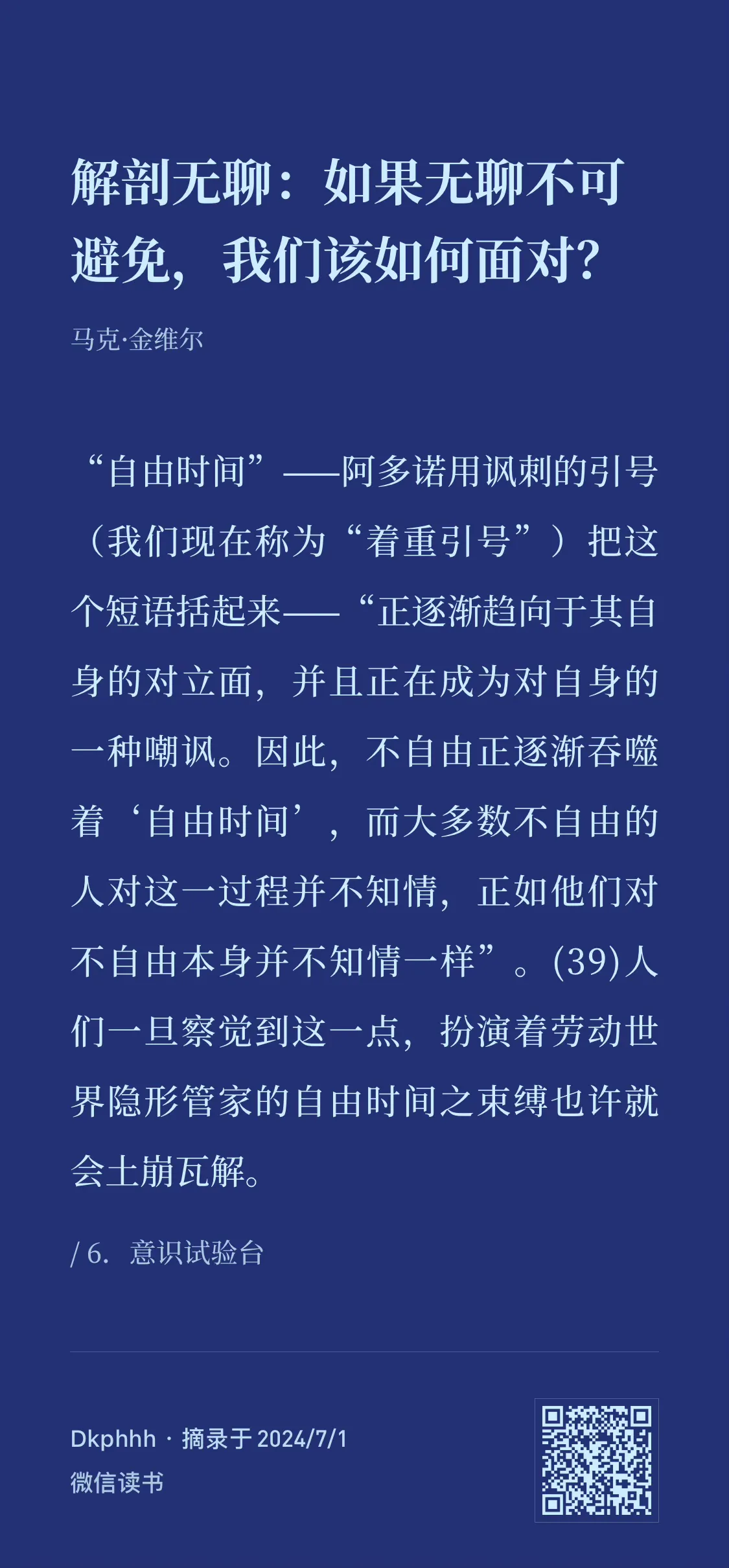
Dkphhh's MurmurCreated@ Mon Jul 01 2024 07:57: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因此,自由时间作为工作组织的时间霸权的对立面,甚至可能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挑战的这种表象,被打破了:事实恰恰相反,两者是同盟者,是同一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双面。“因此,自由时间并不仅仅是和劳动针锋相对。在一个充分就业本身已成为理想的制度下,自由时间只不过是劳动阴影的蔓延而已。” 要打破这种困境,从事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是一个方法。脱离这个社会所有的生产消费循环,只能靠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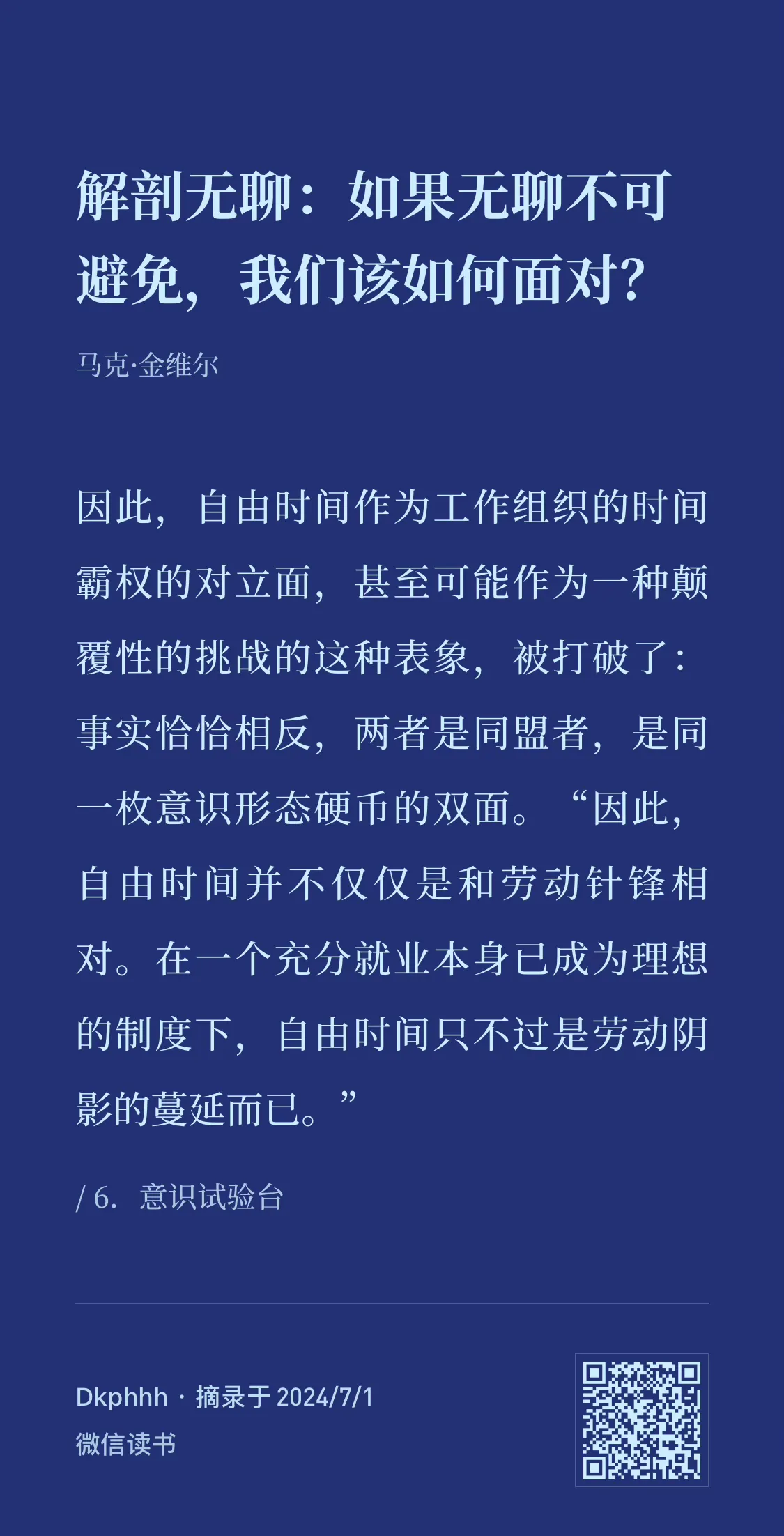
Dkphhh's MurmurCreated@ Mon Jul 01 2024 07:51:00 GMT+0800 (China Standard Time)
事实上,《自由时间》简短而有效地提炼了阿多诺文化批评中所有独特且有趣之处的精华。该文的基本主张众所周知:在后资本主义背景下,工作理念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工作以外的时间也被效用、同化和周而复始的消费循环等命令占据。所谓的自由时间——周末时间或下班后的时间,那些说着“谢天谢地,今天周五了”的时候和休闲时间——其实根本不自由。希腊式理想的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古希腊语中的“σχολή”),意味着除了对终极实在的思考之外,完全无忧无虑的时光。与之不同的是,所谓的自由时间是有先决条件的、绝望的。阿多诺说:“自由时间受制于它的对立面,它所处的对立关系确实赋予了自由时间某些本质特征。”(37) 这些特征包括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自由时间在某种深层或切实的意义上是娱乐性的,而实际上,它为大量错综复杂的工作本身充当电池充电站。阿多诺在这篇文章中继续写道:“(自由时间)取决于社会条件的总和,这种社会条件继续让人为之着迷。” 下班的时间并非真正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下班是为了让你休息,消费,以更好地上班。我们下班也是在为资本主义机器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