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妈妈吃叶酸孩子会聪明。我都给我妈吃了两个月了,感觉没什么效果。
:也许你不是亲生的
:都说妈妈吃叶酸孩子会聪明。我都给我妈吃了两个月了,感觉没什么效果。
:也许你不是亲生的
暂时是业余成年人,这个世界的浅度用户
要是我和这只猫一样可爱就好了,这样就会有人喜欢我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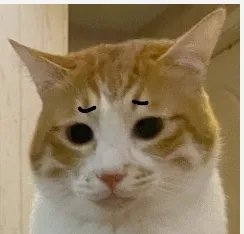
不愿意生孩子纯粹是因为商家售后太差,大家不愿意复购罢了。
我一直很迷恋那种小巧、简单但是用途广泛的东西,比如诞生之初的智能手机,还有瑞士军刀和便利贴。这或许也是奥卡姆剃刀原理在我恋物癖上的延伸。
15 年前的智能手机简直就是我梦想的造物,没有什么比一台能装进口袋的电脑更吸引人了。我喜欢挖掘这些小东西的上限。我尝试过在 4 英寸的屏幕上用 markdown 写东西,当然我失败了,因为小屏幕和虚拟键盘对于持续时间 5 分钟以上的写作就是折磨。我也尝试过用手机制作 4K log 视频,也失败了,无论是拍还是剪都很麻烦。不过,我还是一厢情愿的觉得,这些失败不是它们的上限,而是我的上限。
我也喜欢小巧的影像设备,影像是信息量最为丰富的媒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古井无波的生活过得太久了,我最近很迷恋那种情绪饱满的影像——大哭大笑的人、淹没在金色阳光里的背影、海风机车长头发与修长的手臂,还有浓烈蓝调时刻里的烟火。很俗气,很喜欢,我每天晚上都会看。能随时随地记录这些影像的设备,一定是能随时随地掏出来的口袋相机。一直以来,我的 dream camera 都是索尼黑卡,可惜这个系列已经不再更新。很多人会说手机是记录生活最终的归宿,但手机有一个致命缺陷——没有光学变焦,这让它的记录半径仅仅局限在你肉眼范围的五米内,无法成为替你观察世界的眼睛。
这种癖好一直延伸到我的编程习惯。我最初学习的第一个开发框架是 Django,这是一个大而全的企业级框架,集成了很多开箱即用的方案,包括后台管理、用户验证、对各类数据库的支持,因此它得以支撑着很多亿级用户量的互联网产品,也因此你很难真正的掌握它。为了做到应付各种刁钻的场景和需求,它不得不复杂,复杂就意味着难以理解。
所以我后来又学了 fastapi,它的核心机制一目了然。要做到同样的事情,fastapi 或许要写更多代码,但你知道你面对的不是一个黑箱,会更加自信。我在编码的过程中甚至想自己基于它来实现某些功能(当然事实证明是我想太多了,作者本人早就准备了更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喜欢简单的东西,简单好上手意味着你可以基于已经掌握的机制,自己去探索各种用途和可能性。
简单的作用机制就是一个撬动世界的支点,就像便利贴,你贴在冰箱上就是生活提醒,贴在灶台前就是菜谱,贴在笔记本上就是笔记注解,贴在书里既能是书签又能写批注。简单,易于理解,多用途,这些形容词从来不会孤立存在,一个简单的东西往往就是易于理解且多用途的。
这样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例如 Markdown。Markdown 能做笔记、能排版、还能当作 Todo List 和项目管理工具,但它本质上只是一套文本标记语言罢了,恰恰是因为足够简单,它才能和其他东西搭配在一起,形成如此完善的应用生态。
当然,凡此种种多少都无力招架所谓企业需求,工业化标准,就像瑞士军刀挖不了战壕,但也要知道普通人的生活根本不需要挖战壕。
我没有去伦敦生活,我要讲的是英剧《伦敦生活》
坦率地讲,我很久没看过电视剧了,我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剧迷。这次看这么一部不算热门的剧,是被 B 站上的一条《伦敦生活》混剪视频打动了。 视频借着剪辑拼接的一条条台词探讨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剪辑的作者说爱是被看见。因为“每个人细究起来都蛮有意思,只是人很少有被人仔细看见的机会,以至于被仔细看见这件事,有点近似于爱”。这和我一直以来的观点一样。虽然我一直自嘲自己是一个“偶尔很平庸,一直很无聊的人”,但我也希望自己的小小闪光点有一天能被看见。
我一直很想谈恋爱。我已经快 30 岁了。除了大学谈过一次恋爱,在过去将近 8 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单身。所以我真的很想谈恋爱,我希望在荷尔蒙衰退之前能再尽情体验一次恋爱的感觉,体验那种忘乎所以的冲动。
但我是一个无聊的人,这几年我的生活忙碌又乏味。我每天七点半起床,上班,工作,一直到晚上 8、9 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生活里为数不多的调剂偶尔是几次不算成功的约会,和编程。
对,我喜欢编程。我学编程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当程序员拿高薪,暂时也没有达到高超的编程水平。我学编程单纯就是因为喜欢,喜欢亲手创造的感觉,享受“一个工匠的骄傲和喜悦”。
虽然还不算中年,但我确实察觉到了一丝丝中年危机的味道。或者说,这是我的青年危机。家庭不睦职场不顺的中年人,最后的堡垒是钓鱼。我是编程。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大部分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
蓄谋已久,也要一时冲动
我想过自己的生活,我想要自由
人生是苦难的钟摆,在欲望和无聊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