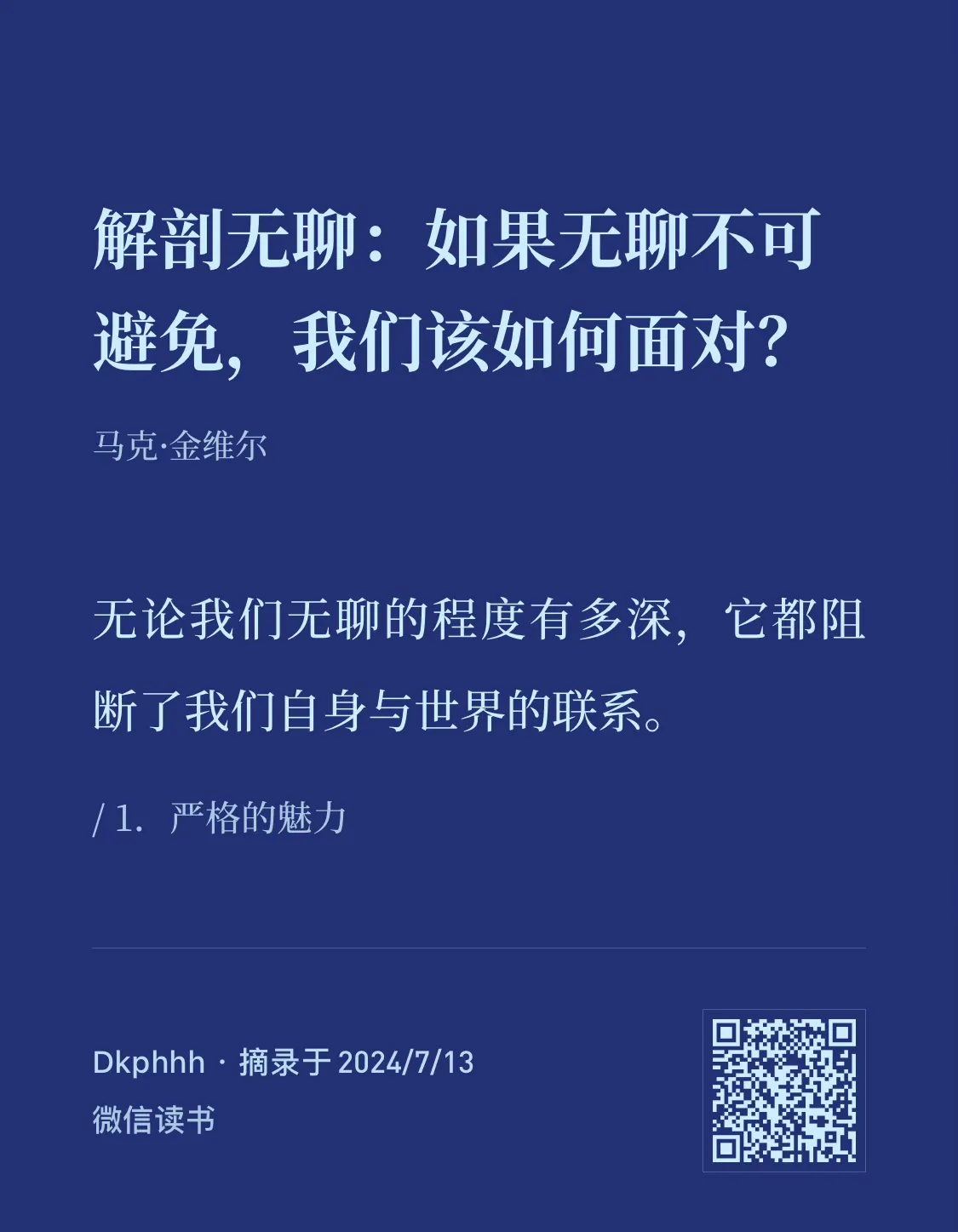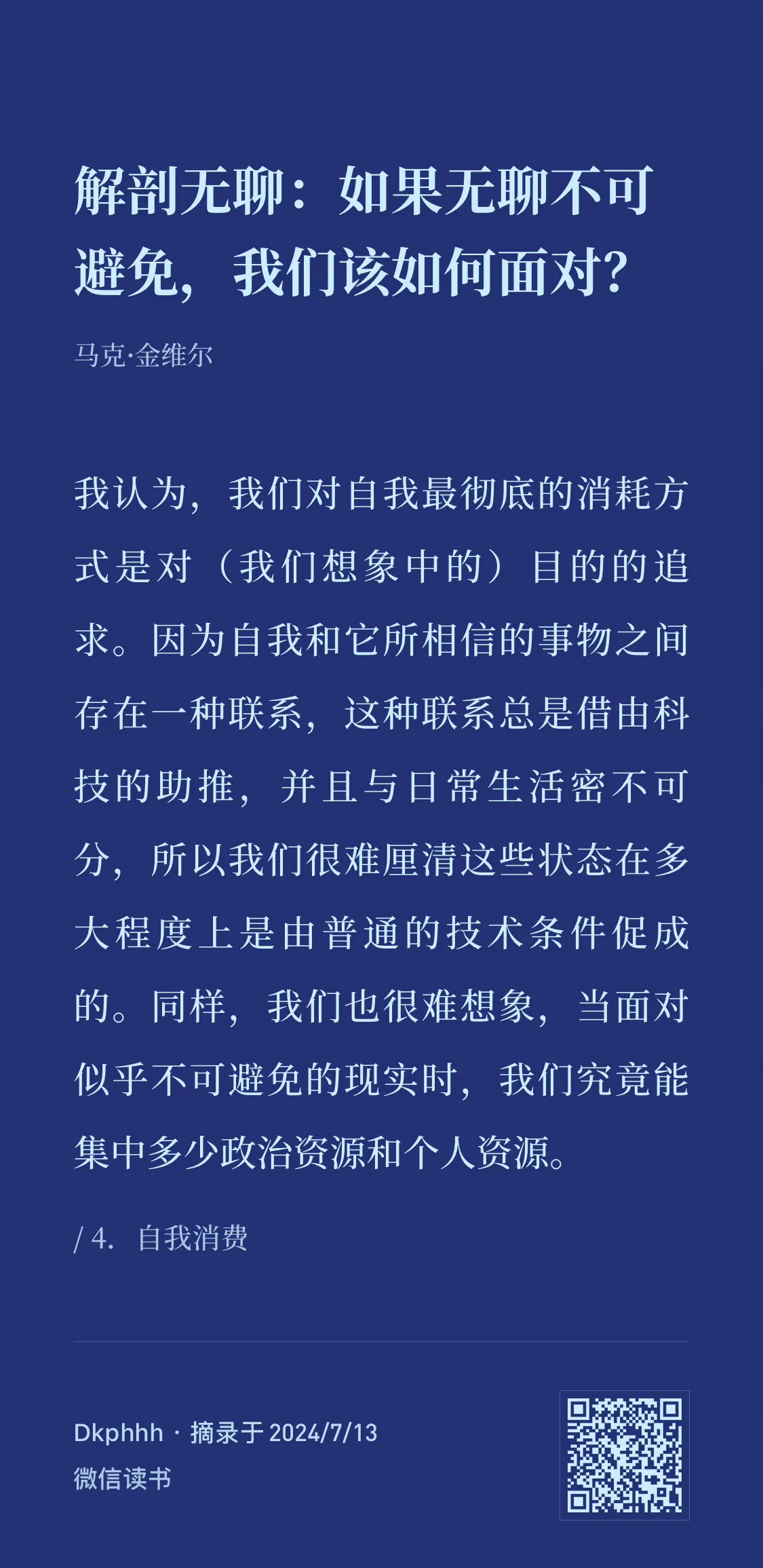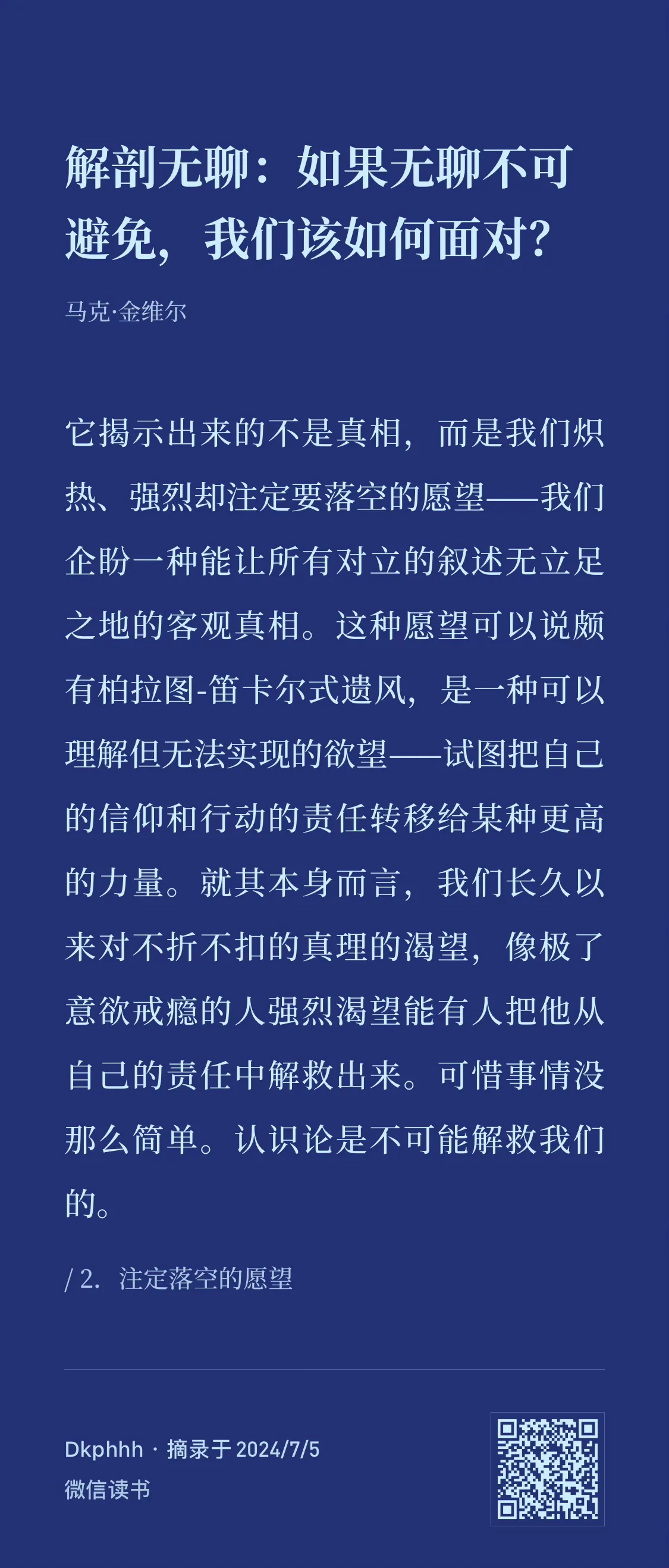从去年开始开的夜宵店,因为工作时间在夜间,人总是容易感觉寂寞,所以没客人的时候总是会聊天。算是不折不扣的深夜食堂了。
我一直有会被人拉着谈自己性生活的属性,不过连我也没有想到,昨天晚上的夜聊,主题是嫖 娼。
我生长在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不少朋友去不熟悉的馆子吃饭都会有点紧张,更不要说去嫖娼了,如果谁胆敢提到这个事情,自然也会被他人以“你这个人档次好低”的眼光看待,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几个人拉着不想去的人一起下水之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嫖娼过的人描述自己的 感受。
两个伙计都来自中部地区,其实外形条件并不差,也都有女朋友,第一次嫖娼都是被师傅或者朋友带着去的。当我询问“为什么有女朋友还会想去嫖娼”的时候,他们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因为和女朋友在一起需要考虑对方感受,但是花钱办事就不用,觉得那样比较方便。
我问:“虽然你们要考虑女朋友的感受,但是女朋友也会考虑你们的感受,嫖娼的时候可不会啊。”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女的有感受,我们男的有什么感受啊。”但是这显然不是真的。我问他们会不会和嫖娼的对象接吻,两人都表示绝对不会,说感觉“脏”。之后两个人一个表述了嫖娼让自己感觉“不好”“有点屈辱”,另外一个年轻的甚至说,自己是先嫖娼再有恋爱经历的,在自己和正式的女朋友有过性行为以后,他感觉很害怕,半个个多月连女朋友的手都不敢拉。其实有这样的表述恰恰说明了他对女朋友的感情是真诚的,所以会觉的自己用“做爱”这件事情侮辱了女朋友。而与此同时,尽管他们隐约感觉到了嫖娼这件事情“好像不好”,但还是拉着不想去的朋友一起去了。
烟,酒,嫖娼,下雨不打伞,不被允许脆弱,不仅自己深陷其中,还要强拉着别人一起。每多了解一点,我就感觉自己更清晰地看到男权社会这些糟粕是如何毁掉人感受幸福的可能性。
我们以往谈到嫖娼的时候,总在从卫生和排他性性行为的层面谈好不好,很少有人从心理层面去看待。但人和人的肢体接触本来应该和关系的进展是同步的,关系好的朋友会拍肩调笑,再好的愿意挽着手一起走,久别的好友会拥抱,亲密的恋人会接吻做爱。而嫖娼的陷阱就在于当事人和自己厌恶的人做着最亲密的事。而这样的经历会毁掉余生中真正亲密和美好的时刻。人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抽离,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放弃尊重和被尊重,其实不能。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从良的小姐会找完全没有收入的男性作为伴侣,因为她们不想再做被买的那个了,曾经出卖过自己的人,很难摆脱自己意愿被践踏的恐惧。
来源:嫖娼心理学_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