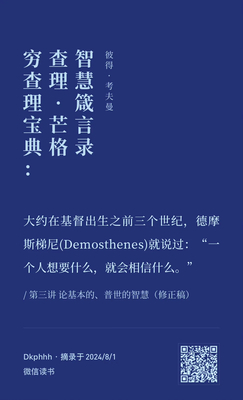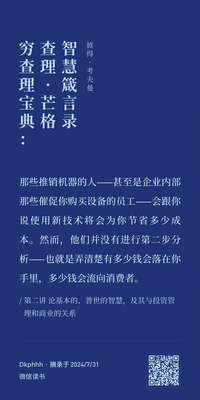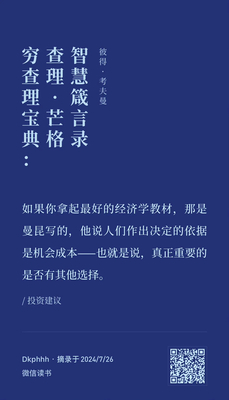不论媒介,最好的作品总像是在对着单独一个人说话。这些作品浓缩着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再跨越时间和空间传达到读者那里,引起强烈的共振。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能够时而带给人难以名状的震撼,从心底感叹这样的作品何以超越这么长久、遥远、迷雾重重的时空,而直接把自己未曾言表的,隐秘、丰饶甚至病态的痛苦和冲动揭露出来。这样的作品一定先在幽暗中产生,再被抛到出版圈、批评圈的探照灯下;如果一直处在公开的光亮当中,它们一开始就无法完成。 来源:互联网时代的创作(上):我们注定不会再有伟大的作品了吗?
从去年开始开的夜宵店,因为工作时间在夜间,人总是容易感觉寂寞,所以没客人的时候总是会聊天。算是不折不扣的深夜食堂了。
我一直有会被人拉着谈自己性生活的属性,不过连我也没有想到,昨天晚上的夜聊,主题是嫖 娼。
我生长在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不少朋友去不熟悉的馆子吃饭都会有点紧张,更不要说去嫖娼了,如果谁胆敢提到这个事情,自然也会被他人以“你这个人档次好低”的眼光看待,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几个人拉着不想去的人一起下水之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嫖娼过的人描述自己的 感受。
两个伙计都来自中部地区,其实外形条件并不差,也都有女朋友,第一次嫖娼都是被师傅或者朋友带着去的。当我询问“为什么有女朋友还会想去嫖娼”的时候,他们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因为和女朋友在一起需要考虑对方感受,但是花钱办事就不用,觉得那样比较方便。
我问:“虽然你们要考虑女朋友的感受,但是女朋友也会考虑你们的感受,嫖娼的时候可不会啊。”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女的有感受,我们男的有什么感受啊。”但是这显然不是真的。我问他们会不会和嫖娼的对象接吻,两人都表示绝对不会,说感觉“脏”。之后两个人一个表述了嫖娼让自己感觉“不好”“有点屈辱”,另外一个年轻的甚至说,自己是先嫖娼再有恋爱经历的,在自己和正式的女朋友有过性行为以后,他感觉很害怕,半个个多月连女朋友的手都不敢拉。其实有这样的表述恰恰说明了他对女朋友的感情是真诚的,所以会觉的自己用“做爱”这件事情侮辱了女朋友。而与此同时,尽管他们隐约感觉到了嫖娼这件事情“好像不好”,但还是拉着不想去的朋友一起去了。
烟,酒,嫖娼,下雨不打伞,不被允许脆弱,不仅自己深陷其中,还要强拉着别人一起。每多了解一点,我就感觉自己更清晰地看到男权社会这些糟粕是如何毁掉人感受幸福的可能性。
我们以往谈到嫖娼的时候,总在从卫生和排他性性行为的层面谈好不好,很少有人从心理层面去看待。但人和人的肢体接触本来应该和关系的进展是同步的,关系好的朋友会拍肩调笑,再好的愿意挽着手一起走,久别的好友会拥抱,亲密的恋人会接吻做爱。而嫖娼的陷阱就在于当事人和自己厌恶的人做着最亲密的事。而这样的经历会毁掉余生中真正亲密和美好的时刻。人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抽离,只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放弃尊重和被尊重,其实不能。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从良的小姐会找完全没有收入的男性作为伴侣,因为她们不想再做被买的那个了,曾经出卖过自己的人,很难摆脱自己意愿被践踏的恐惧。 来源:嫖娼心理学_微博
现在突然对所谓的「永久保存」没什么执着了。 信息的永久保存在这个时代真的有意义吗? 如果我需要找某个信息,例如撰写 prd 的格式和方法,我不必纠结于要找到特定某一篇大家都说好的教程,我只需要在 Google 检索,找几篇看着像样的学习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查找某一篇经典的网络文章,即便原链接已经失效,网上也会有人转载和存档。如果没有,说明不够经典。
张潇雨谈如何确定自己喜欢做的事 没事儿做点思想实验挺好的,刚才临时起意出了一个,可以玩一玩。 还有另外一组我觉得很经典的思想实验,之前在播客里也录过一期节目,是关于“如何判断自己喜不喜欢做一件事的”。描述如下:
- 如果此刻就把做这件事的附带结果都给你,你还愿意继续做它吗?比如你正在为了减肥 20 斤跑步,但如果现在立刻你就能比较健康地瘦 20 斤,你还愿意跑步吗?
- 如果有一件事你只能默默做,不能告诉任何人,你还愿意做它吗?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 假设你有两件喜欢的事,A 和 B。现在突然来了一个外星人说,它可以给你提供无限的资源,在你剩下的人生里慢慢帮助你把 A 做好,但前提是你这辈子再也不能做 B 了。你愿不愿意答应它?
- 最后,如果你注定十年后的今天会死掉,那么你还愿意做这件事吗? 人生未来好几十年,都可以时不时拿出这几个问题来问问自己。 来源:张潇雨谈如何确定自己喜欢做的事 没事儿做点思想实验挺好的- 即刻App
书里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个原理,目测是其他竞争对手会跟进,成本优势难以维持。
那些推销机器的人——甚至是企业内部那些催促你购买设备的员工——会跟你说使用新技术将会为你节省多少成本。然而,他们并没有进行第二步分析——也就是弄清楚有多少钱会落在你手里,多少钱会流向消费者。
第一次知道
原来在互联网的规则中,外界给你发送任何信息,接收端必须得在 3 天 72 小时内处于可接收状态,信息才会收到。如果超出这个时限,那这些消息就会像掉进大海中的石子,再也没有找到的可能了。 来源:不用手机,134天,我的环游中国记
今日职场吐槽:在一个公司里,能永远不犯错的人,只有老板。因为一个人只要在做事,他就有可能犯错,老板不做(具体的)事,他就不会犯错。当然,这不意味着老板真的不会犯错,只是老板做的事(或者叫决策),大部分反馈周期比较长,不容易被“抓现行”。
还有如何衡量不同工作的价值,比如一种偏见是白领高于蓝领。但哲学家会说这是一种 “精英的傲慢”。我们应该恢复工作的尊严,将人看作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每个人都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从而赢得认可。这是维系民主社会团结的纽带。[12] 在这一问题上,阿西莫格鲁的立场更像社会学家或者哲学家。他觉得,工作对于人类的心理、社会互动和自我价值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将正义简单视为人们有足够食物或者舒适生活,更好的正义观念是所有人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但如果没有工作,这将非常困难。” 他说。 来源:从无人车到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技术进步的 80 亿种可能
需要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具有大量机动性和灵活性的熟练工,比如管道工或电工。自动化这些工作需要科幻级别的机器人,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 C-3PO 。“这是机器人领域最困难的挑战。我认为这些工作要很长时间后才受到威胁。” 福特说。
主流经济学对技术进步后果的回答是,新技术虽然会消灭一部分工作岗位,但也会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这会存在一个经济规律自动调节的过程,不必担心。[6] 所谓自动调节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个是 “补偿”。比如新技术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提供更好服务或者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公司对劳动力的需求。典型例子是自动取款机(ATM)在 1990 年代美国推出后,并没有减少银行柜员数量。相反,它使银行能够开设更多分支机构,柜员数量实际上增加了。[7] 另一个是 “互补”。比如人们会学习如何使用新技术,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这也是人类与机器互补、融合或者协同进化的过程。[8] 乔布斯曾把个人电脑比作 “大脑的自行车”,微软的纳德拉则说 AI 像 “大脑的蒸汽机”。 但是,“补偿” 或者 “互补” 都存在缺陷。 “补偿” 的缺陷之一是无法保证 “需求” 调节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能在短期内完成,别忘记工业革命初期的过渡以三代英国工人为代价。“互补” 的缺陷之一是高估每个人的能力。事实上,只有少数人能够顺利掌握新技术,大部分人都会落伍。[9] 来源:从无人车到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技术进步的 80 亿种可能
AI 要自己取代人类还是科幻,但一些人用 AI 取代另一些人,是每天在发生的事。 来源:从无人车到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技术进步的 80 亿种可能